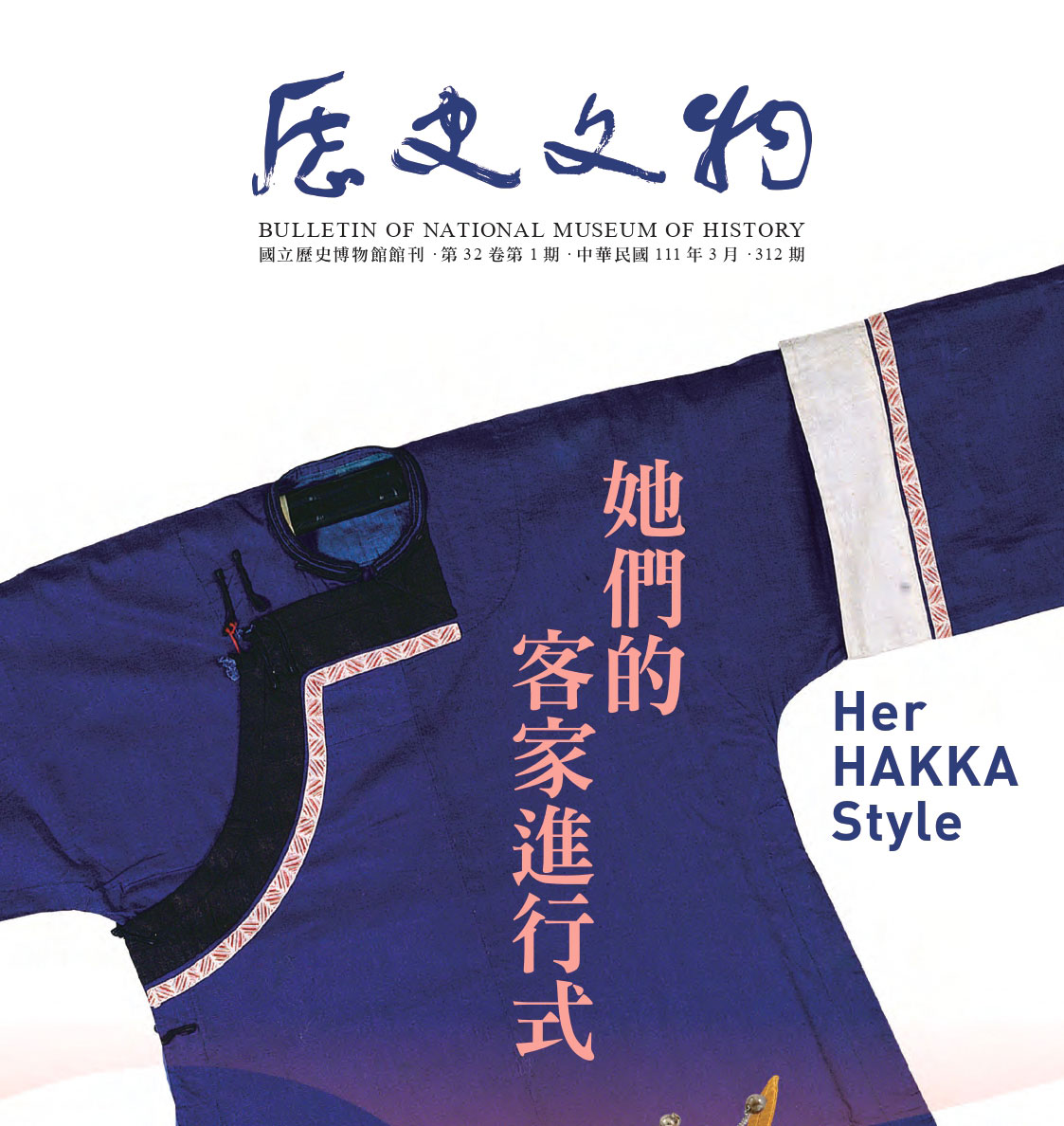(本文摘錄自《歷史文物》325期封面故事)
文|陳思宇採訪
圖|史博館、東京大學綜合研究博物館
蘭花是臺灣人日常生活中熟悉的存在,無論是市場裡的盆栽、祭祀的供品,還是國際園藝展上的亮眼代表等。然而,其背後實則交織著跨國的知識系統與複雜的視覺文化脈絡。

國立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史博館)「臺灣蘭花百姿」特展,正是一場回看臺灣蘭花意涵的展覽,透過植物標本、科學畫、藝術品與歷史圖像,重新爬梳蘭花在臺灣歷史與文化中的位置。本展由史博館與日本東京大學綜合研究博物館(以下簡稱東大博物館)共同策劃,結合臺日研究者與館藏資源,開啟國際共製的展覽實踐,先後於東京及臺北展出。展覽首站於今(2025)年 2 月在東京丸之內 KITTE 大樓的「INTERMEDIATHEQUE」登場,接續臺北展則由史博館進一步擴展內容,從臺灣視角梳理蘭花圖像的文化系譜。本文也透過專訪史博館陳奕安,深入展覽的脈絡與策展思路,窺見蘭花如何在多重殖民與現代化過程中,成為臺灣植物視覺文化的一部分,也理解當代博物館如何以在地觀點參與跨國共製。
臺日合作的契機與挑戰
「蘭花百姿」起初由東大博物館策展人寺田鮎美(Terada Ayumi)策劃,名稱發想自幕末明治時期,浮世繪大蘇(月岡)芳年(Taiso Yoshitoshi,1839-1892)的《月百姿》。此作品描繪與月亮有關的故事和傳說,不過並不直接以月為主角,而是將月作為一個共通的抽象背景來串聯起各式各樣的題材,具備如百科全書般「博物誌」的世界觀。可以說從展覽發想的初始,她就有意以跨越科學、藝術與文化的百科全書式視野,活用東大博物館的科學收藏,探討「蘭」的多種面貌。

史博館的部分則由館內策展人陳奕安操刀。談起這個展覽的合作契機,當時陳奕安於日本求學,在一次分享會上介紹史博館的豐厚館藏,並提出「梅、蘭、竹、菊」等植物在文人畫中的特殊意義,讓策展人寺田鮎美捕捉到合作的契機。陳奕安也認為如果能有機會以新的視角在展覽中呈現史博館的館藏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不過,跨國展覽當然不能只是移植日本的研究,畢竟不論是在殖民歷史還是文化脈絡上,日本與臺灣都具有極大的「視差」,她認為在策劃過程除了要對藏品重新論述與詮釋外,更重要的是凸顯臺灣視角的獨特性。
臺日兩位策展人,因此在對「蘭花百姿」這個概念取得共識的前提下,開始合作拓展「臺灣蘭花百姿」的概念。在共同展品的選擇上,為了更豐富展現臺灣的蘭花圖譜,除了與臺灣典藏有相關美術作品或文獻的國立臺灣博物館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美術館、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等館所借展外,亦自植物研究角度,從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植物標本館與農業部林業試驗所植物標本館等,特別商借日治時期留存的植物標本、乾版玻璃底片等展出。陳奕安表示,在策展過程中,兩人貫徹「博物誌」的精神,從與臺灣的蘭花相關的各式脈絡展開蘭花展品搜尋,結果發現蘭的形象,遍布臺灣歷史上繪畫、工藝、攝影、設計等作品中,讓兩人切身地發現,蘭花作為一種象徵意義持續轉換的符號,緊密地滲透在各階段臺灣文化的縫隙,展現了我們獨特的社會情狀。
日治時期的科學畫與繪葉書
若欲理解今日我們對蘭花的想像,必須回溯至臺灣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植物學發展,以及其中現代化歷程與媒體再現的影響。展覽的第一部分聚焦於植物學研究中臺灣蘭花與植物學家們的角色,進一步透過標本與「科學畫」呈現蘭花作為研究對象的視覺化過程。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期間,田代安定(Tashiro Yasusada,1857-1928)、早田文藏(Hayata Bunzō,1874-1934)、瀨川孝吉(Segawa Kōkichi,1906-1988)等植物學家採集並整理了大量植物標本,為臺灣近代植物研究奠下基礎。由於乾燥標本的植物特徵常因脫水烘製而伴隨細節失真,以重現植物細節與特徵為要的科學畫,便必須與腊葉標本相輔相成,也在此形塑了早期植物科學中的蘭花形象。
陳奕安指出,科學畫的繪製背後有一套精確的知識系統,必須在高度寫實中凸顯植物形態的差異性。畫家須盡可能還原植物的真實樣貌,並描繪出其與其他近似物種的辨識差異,包括葉形、花色、種子結構等都屬關鍵資訊。此次展出作品之一、1930 年代由山田壽雄(Yamada Toshio,1882-1941)繪製的《臺灣蝴蝶蘭、虎斑蝴蝶蘭》及《燕石斛、紅石斛、金石斛》,便是極具代表性的範例。畫作極為細緻地描繪蘭花的花瓣、葉片、果莢等結構,在色彩與造型的處理上也極為講究,不僅展現繪者對植物的深刻觀察與理解,體現當時科學圖像製作的嚴謹精神,更具有讓人難以忽視的藝術性。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殖民統治初期,臺灣總督府發行了非常多以蝴蝶蘭為設計符號的宣傳品。「蝴蝶蘭」的漢字用詞,最早可以追溯至田代安定在蘭嶼踏查時筆記本上的紀錄。
蝴蝶蘭除了是臺灣原生種之外,更陸續被鑑定出兩個臺灣特有種。對當時的日本人來說,具有異國風情且姿態優美的蝴蝶蘭是非常珍稀且受到喜愛的植物。在日本帝國統治下的殖民地發現特有種蝴蝶蘭,在科學研究的突破與殖民統治成果等方面,都是日本成功追隨當時歐洲列強帝國發展模式的象徵。在日本統治臺灣初期,現代化建設尚未齊備之前,蝴蝶蘭的形象,就成為殖民政府宣傳成績的一大象徵。在這次展覽中,臺灣總督府第 12 屆始政紀念明信片「新高山」及第 13 屆始政紀念明信片「恆春廳石門」,蝴蝶蘭形象都被用作視覺設計上的亮點。
另一方面,陳奕安也提到,若以臺灣的視角來看,這些運用蘭花符號的明信片,也反映了臺灣受到日本殖民統治的不同階段。以 1908 年印製的「恆春廳石門」為例,上面記載有日軍出兵的功績,圖案描繪的是日本統治臺灣以前,首次成功系統性對臺用兵的「牡丹社事件」。另外還有「新高山」、「臺灣縱貫線鐵路全線通車紀念」等明信片,皆由總督府以紀念其始政臺灣為名發行,分別凸顯日本在臺地理探勘與鐵道建設的成果。這些日治時期的印刷物,可以讓我們以今日的眼光,認識到臺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從一開始受到軍事壓制,到全島進入日本的科學研究視野,及至後來現代化建設遍布全島的歷史。而在這樣的過程中,臺灣特有種蝴蝶蘭,作為設計符號的角色持續登場,傳達的不僅是一段殖民歷史,更是今日臺灣蘭花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個成分。
臺灣蘭花百姿-臺北展
展期|2025.07.08-09.07
地點|國立歷史博物館
(本文由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歷史文物》授權摘錄轉載,完整文章請見《歷史文物》325期)
更多本期精采內容,請見《歷史文物》精華版電子書
購買由此去:
國立歷史博物館博物館商店:臺北市南海路49號
TEL:02-2388-2782
五南文化廣場臺中總店:臺中市中山路6號
TEL:04-2226-0330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臺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TEL:02-2518-0207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