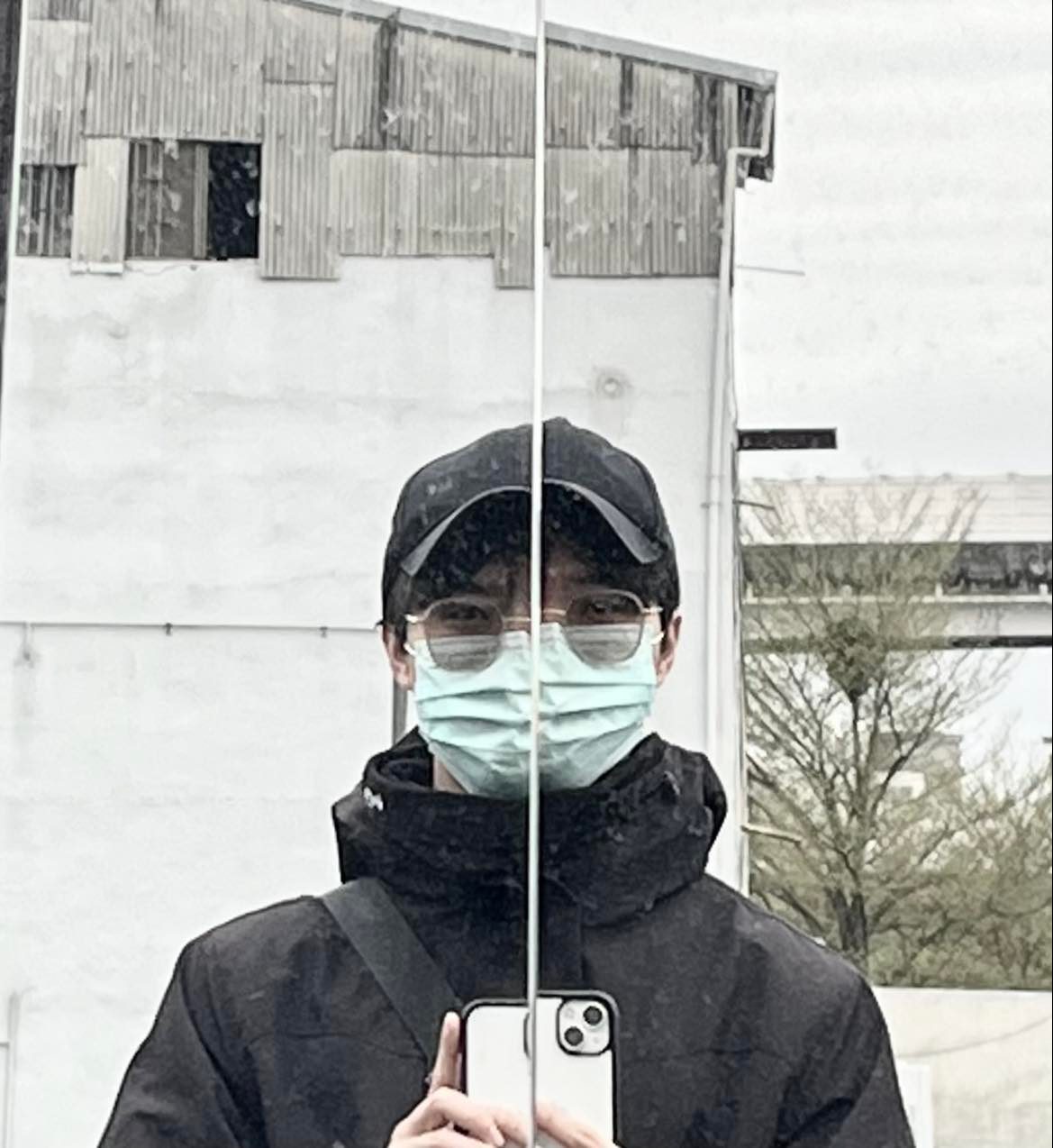就讀大學美術系之後,對於從事藝術的人們做過或正在做些什麼,依舊保持著濃厚的興趣。除了書籍和網路上的文章資料之外,我也透過社群網站瀏覽藝術工作者的動態。這些內容通常不會被書寫記錄,卻有著最真實的一面。儘管人際關係並不是解讀展覽或作品的關鍵,卻是我對藝術社群更細緻理解的渴望。
每天滑一下臉書和IG,就像是一段速寫的時光,紀錄那些散碎紛雜的資訊片段。從新作發表到日常碎念,以及各式活動貼文和留言互動,都收集到腦中那貼著「藝術」標籤的資料櫃,積累成層次混雜的檔案系統。

從美術班到美術系,持續探知的觸角
當我非常嚮往、熱愛某些人事物時,就會對其相關資訊特別關注;而當有機會分享時,總是顯得特別興奮,進入一種「宅宅」狀態,就像《我的英雄學院》裡、筆記本寫滿職業英雄資料的綠谷出久,或是《一拳超人》中總是抱著英雄圖鑑的鼻涕雄。而這種習慣也對我學習藝術至今的歷程產生影響。
自高中時期開始,我便透過數位社群觀察其他美術科班的情況,初步建立對環境的認識,並且在升學過程中接觸到當代藝術領域。進入藝術學院後,依然保持著在社群上關注藝術相關資訊的習慣,在學院裡經歷不同課程和師長,不斷衝擊、再建構藝術觀;而在參與美術系系刊《刊霧啟事》以及同儕自組的《Sketchbook》等刊物製作的過程中,又認識到不同媒體的能力(與魅力),進而開始思考,自己這個世代的社群運作狀態和可能為何。
在高中階段,除了鑽研喜愛的媒材和形式,例如水彩和寫實繪畫,也花了許多時間在網路社群上觀察其他學校美術班,也為此跑到外縣市看展覽。在網路瀏覽與實際走訪的過程中,我注意到同地區學生的作品會有著類似的調性或手法,像是用筆用色的方式,乃至於構圖和題材。地區風格的形成,蠻大程度上受到地方畫室和學校教師影響,我偶爾也藉此從創作者的作品中,推測其養成來源。
會報考藝大,是因為升高三那年(2018)和同學一起看了北藝大美術系畢業展「稍縱即逝堡」,面對看不懂內容的投影,或是空間與動力裝置,種種以往所不熟悉的藝術樣態,改變了心底對創作生涯的想像。在那之前,對大學相關系所只有「某校偏傳統,某校偏當代」的籠統認知,那檔大學畢展,可說是我開始關注當代藝術的契機。
在美術班時期,觀察外界的驅力來自於一種比較的心態,藉著閱覽各地區學生的作品來認知自己的程度,不過關注範圍主要是繪畫作品,或有關術科考試能力的練習。進美術系之後,關注則轉向「這個環境的人在做些什麼?」、「環境中被觀看和討論的創作、展覽或事件是些什麼,以及如何被討論的?」細究這些觀察點,其實含有對自己未來創作路線與狀態的不確定。歷經學院課程、展覽、媒體等管道,見識了各種實踐的可能,然而吸收到的資訊越多,就越常有種選擇障礙的感覺:做創作的意向明確,但作為創作者的樣貌還在摸索,思考自己的定位。


創作的理由:養成、擱置到路線開發
進美術系就讀後,即面臨到許多觀念的刺激與提問。像是在基礎必修的「素描」課中,就必須嘗試回答什麼是「素描」,或是選擇創作形式的理由;對大部分美術科班背景的人來說,其中一個深刻的問題大概就會是「為何(還)選擇繪畫?」除此之外,高俊宏老師的「計畫型創作」則是讓我有深刻感受的另一門課。在初認識這類常以研究為基礎、不以處理感性或美感造型為主要目的創作時,歷經了一段對自身創作蠻激烈的質問:關於創作的題材或處理方式的社會性、觀念性等,也對當前藝術環境部分的議題傾向更有認識。
繪畫是一路養成上來最熟悉且理所當然的創作方式,面對這種對創作根本的提問,有些人和我一樣,在無法圓滿自答的狀態下,同時抱著嘗試其他類型創作的心態,而減少了在學院裡發表繪畫作品的次數。在北藝大這般有著特定教養的當代藝術教學環境裡,似乎更讓人在意繪畫的理由。直到近期參與了三次和臺藝美術、元智藝設的「三校繪畫大PK」,以及和畫家楊立的接觸交流,刺激我重新思考自己與繪畫創作、繪畫與當代藝術之間的關係。
這些活動與北藝大的課程或評圖不同,評鑑普遍給人一種氣氛緊繃的印象,彷彿要上戰場,準備接受生死宣判。除了視覺呈現和概念,口頭報告時的表達狀態也十分影響老師們的回應內容。有些人就能像聊天一樣和評委對答,也有人在情緒緊張的情況下,將中性的提問解讀成質疑而有較大反應;而對創作觀有強烈主見的外評,針對創作動機或內容的批評意見,亦會對學生造成不小的影響。「PK展」則是個純粹討論「繪畫」而非概念的場合,參與活動的師長、前輩與同儕們,針對造型、佈局、畫法、質地等面向進行交流與討論,這種狀態在北藝是較少見的。

檢視自己目前的狀態,是把「繪畫」和「其他類型創作」分成不同的軌道。對我來說,繪畫有它獨有的能耐與任務,是我在其他類型創作無法處理到的,內容上也往往關聯甚遠。如果以「繪畫獨立」的立場來說,「畫家」和「藝術家」不同,更強調特定能力的區別和投入程度,那以我的狀態,或許可描述成「喜歡繪畫、並有點繪畫能力的藝術家」;若將繪畫視為一種專業能力,就如同有人同時是導演 / 平面設計師 / 藝術家,那我是否能以藝術家 / 畫家的身分被認知?
我期望作為一個面向豐富的創作者,並讓各類作品在合適的場域中被觀看與討論。在「PK展」,我純粹處理自身面對繪畫的問題,不管是針對特定題材或是畫法試驗,藉此機會提出,與從事繪畫的人深入討論;而在系上評鑑,我傾向發表繪畫以外的作品,例如空間裝置、版印物件、書籍等跨媒材與形式的創作,因為在這個環境,比較適合以所謂當代藝術的思維討論這類型的創作。會有這樣分別的狀態,來自於一種對於自學院時期起,就被期待將創作整合為單一軸線與思路的抗拒感。我更期望能依據創作類型,個別放在不同的身份、介面與環境中進一步養成、訓練。

組不成團體的話,就多開幾個群組吧?社群媒體連結創作同好
大三時開始參與系刊的製作,做了一些訪談的企劃,其中包含訪問美術系的學長。在訪談過程中,除了逐漸了解到美術系過往的情況,也發現2014年的318學運影響了不少當時的美術系學生,使許多人在日後常以團隊的方式在藝術界活動和工作。然而學院的多數人都還是習慣單兵作戰的方式。自我這個學年往上算三屆,曾有過如「泥濘派」、「無光計畫」等學生自組團體,不過運作時間相對較短,大學畢業後也未有持續活動。目前在大學部尚未看見學生自發組織的情況,但有同儕合作出版集合發表有關自己創作的「素描」或主題研究的刊物《Sketchbook》,又或是自組聯展、讀書會、分享訊息的群組等,算是較接近「藝術團體」型態的交流圈。
近年雖較少有同儕自發的創作團體,但以刊物出版為形式的共作,為學院創作者提供了不一樣的藝術養分。出版有種間接狀態,讓編者與讀者以此距離碰觸他人的創作,此種距離能讓個/群體之間不必有很熟絡的關係基礎,也得以交流。刊物邀請創作者透過書寫、影像、圖文,分享各自的創作思考甚至困頓疑惑,在更了解彼此的狀態下,討論將更加真誠實在。這種的類共學社群,可能是目前學院工作室文化、評圖評鑑制度與課堂學期之外,較特別的藝術養成場域。
「學院不(該)是年輕藝術家的競技場。」這句系上老師曾分享過的一句話,兩年多來不時浮現腦海。創作者自然都會想要突出,但若僅專注在耕耘個人志向,有點可惜了同時和這麼多創作同儕交集的時期。若將學院視作實驗場和交誼廳,學生可以更遊戲的心態嘗試藝術實踐,配合網路社群可發表、交流、串連等特性,或可爲環境注入更多能量。
延伸閱讀|【給Z世代的藍色時期】不小心按下重置鍵:策展以外的身份思考
(責任編輯:陳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