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於傳統影院觀影模式中,觀眾和影像之間多半只是疏離的觀看關係,甚至只是一種影片甫播畢、演職員表出現的瞬間人們便紛紛離場的「冷交換」關係,以美術館空間展示電影更有機會催生出人與影像之間的「熱交換」場景。從先前的「來美術館郊遊」到今年的「無無眠—蔡明亮大展」(以下簡稱「無無眠」展),同時身兼策展人與導演雙重作者身分的蔡明亮,充分印證美術館空間遠比場次多半屈指可數的傳統映後座談,更有機會悉心看顧及呵護所有熟悉或不熟悉他的觀影者;藉由美術館的展呈框架暨教育活動平台,蔡明亮重新找到他的電影迷戀與觀眾熱情交會的新契機,而後者也獲得閱讀其影像美學的全新路徑。

「來美術館郊遊」展場照。(攝影/黃宏錡,北師美術館提供)
由此觀之,宣稱在《郊遊》之後不再拍攝劇情長片,轉而創作愈來愈多影像裝置、實驗短片,乃至於劇場作品的蔡明亮,早就不再侷限於電影導演的身分,其多向度的創作觸角也已深入動態影像與多重時間、空間佈置(dispositif)之藝術範式的全新探索領域中—他就是一位靈活運用影像、聲音及空間裝置的成熟藝術家,而我們正目睹他創作生涯的重大轉向,而非「轉進」。倘若如此,展覽手冊中的核心提問:「在美術館看蔡明亮電影,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其實是個在不遠未來勢必會漸次失去效力的問題意識;只要藝術家的企圖心沒有止步於電影的美術館化,只要他的創造性沒有停留在影像放映場所的移置與轉化上,某種超越常規的電影影像思維,以及既有錄像裝置語彙的藝術新範式,似乎是可以期待的。藝術家的影像之思,究竟催生哪些原本電影與視覺藝術領域都不曾擁有的影音佈置、觀影模式抑或感覺結構?而在這條跨域荊棘路上,總是扮演著影像美學孤行者的蔡明亮,究竟引領我們走了多遠?這些都是亟待回答的嶄新問題。

「無無眠—蔡明亮大展」展場一景。(攝影/黃宏錡,北師美術館提供)
置於「永恆」台座上的電影影像
當代美術館空間的投映條件建立在數位投影機的問世上,但實現超長時播映的技術性革新所帶來的改變,並不只是回應了錄像裝置類展覽的現實要求—意即不同於影院的固定場次播映模式,只要在開館期間,任何時段走進美術館的觀眾都能置身在影像的時延(duration)之中;在今天,早已成為基礎常規的循環播放功能,其實也改變了影像的時間性,以及人與影像之間的可能關係。簡言之,雖然絕大多數錄像作品都仍有片頭和片尾之分,但為了達到觀眾隨時隨地都可看到影像的基礎要件,任何在美術館空間中展示的影片都必須展延成一種「沒有真正開始也沒有真正結束」的影像,猶如古代煉金術的重要徽記「銜尾蛇」(Ouroboros)的形象一般,首尾相接,在無止盡的自我重複之中,影像的時間也延展至無限—這正是美術館展呈框架帶出的嶄新條件:影像的永恆回歸(eternal return)。
相較於影院基於商業邏輯將時間予以切分、規格化,好一個場次一個場次地販售的快步調節奏,美術館提供的是可以反覆凝視、散步、喘息、沉澱的超長時間,因為它給予每一位觀眾的正是「影像必定會迴返」的堅實承諾。再者,不同於影院空間總有著若不在指定場次內(正襟危坐地)看完電影,就必須再買一次票的無形壓力,美術館空間本就是一個從不限制觀眾何時看展、何時離開,任憑其自由決定專注時間長短與身體動線的漫遊者式空間;一個只要你願意,展覽期間你可以無止盡地與影像長相廝守的迷戀空間。在此,影院式的兩小時切分會顯得太短、太倉促;然而蔡明亮的緩慢影像卻可以在這種展呈框架內順利攤展,宛如生活中閒散的飲水、呼吸、步行一般正常。

「無無眠—蔡明亮大展」展場一景。(攝影/黃宏錡,北師美術館提供)
雖然「無無眠」展仍舊採取傳統影院的場次播映模式,但實際上它早已置身前述這種銜尾蛇式的時間性邏輯:如同蔡明亮在二樓留言板上寫下的話「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想睡就睡;想走就走」,展覽對於觀影模式的不設限,正是為了跳脫傳統影院那種著重連續性、整全性、不可逆的線性時間。觀眾或坐或臥、或專注或分心地與其影像長時相伴,已漸漸走向一種解構的、遞迴式的、無限復返的摺曲式時間。正因為影像永遠都在那裡,即使錯過了它也必定會迴返,無論清醒還是昏沉,我們始終「在影像的時延之中」。於是,一種令人打從心底放鬆、安適的自由觀視狀態便浮現了。那些相信唯有傳統影院束縛狀態才可能高度專心、嚴肅地觀影的人,或許會質疑「無無眠」展的安排只會導致鬆懈與散漫的看展心態。但此種批評可能忽略了,傳統美術館機制原本預設的就是一種在緩慢、沉澱、心無旁騖的狀態中,將專注力僅僅匯聚在觀看對象身上,無關乎利害地進行靜觀凝視(contemplation)的經驗。這種觀看方式與蔡明亮日漸純粹化的影像之思甚是合拍。即使不談如此古老的美感鑑賞模式,「無無眠」展也嘗試在基本的身體狀態上引導它的觀眾。有機會在影像旁側躺下來的人們不難發現,身體一旦變得柔軟與沉靜,無論是小康在大馬路邊的緩步前行、安藤政信(Masanobu Ando)於澡堂內洗刷身體、電車窗框的閃動、熱水池的蒸霧、桑拿室裡的汗滴,還是膠囊旅店裡的輕微呼吸起伏,這些細節變化全都與我們的身體一起共振著。觀影狀態的改變使得心理上的時間感受也跟著緩慢下來,於是,藝術家的影像顯得一點也不慢,它們不過是真實時間的自然流逝。
從過往影像裝置的空間佈置中退行
不過,「無無眠」展的空間處理確實引起一些爭議,部分批評者質疑它對美術館空間的運用過於簡約。不難理解,這是因為從2004年的《花凋》、2007年的《是夢》、《情色空間》開始,一直到前年的「來美術館郊遊」,蔡明亮其實已形塑出一條鮮明的影像裝置創作脈絡。熟悉這些作品的觀眾,完全曉得他過去如何透過虛實影像的配置串連起電影場景與真實空間之關聯,並且藉由不同投映介面的交錯,將其影像之思轉化為可觸可感的存在。如《是夢》特地將放映屏幕與多把留存導演兒時記憶、來自馬來西亞一家舊戲院的紅色座椅裝設在一起,使得造形影像能與物件之觸覺性相互呼應,共同召喚一種複合式的身體感知經驗。又或者先後在故宮、國美館展出的《情色空間》,迷宮式的空間格局一方面明確指向蔡明亮電影創作中的諸多符號與場景(如1997年《河流》裡的三溫暖空間,或者2006年《黑眼圈》及「來美術館郊遊」現場都曾出現的廢棄床墊),另一方面也誘導觀眾以親身體驗自行演繹、填補導演在裝置中刻意懸缺的空間敘事。誠如影像研究者江凌青所說,這種裝置佈置策略的特出之處便是影像的「以退為進」,裝置雖然不以影像為主體,但觀眾反而更能充分感受「…整座空間如何像是蔡明亮電影中的那些長鏡頭,慢慢地浸染了視線、鑽進了髮膚時,他們不僅是為裝置藝術在美學意義上所經常處於的『未完成狀態』進行填空的動作,更是以跳脫一般影像裝置的感知模式(如同葛羅伊斯(Boris Groys)所言的,以動態狀態追逐運動影像),來重新檢驗他們對蔡明亮電影作品的視覺與感官記憶。」(註1)

蔡明亮作品《是夢》於台北市立美術館「斜面連結」展覽現場一景。(台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蔡明亮的影像創作時常展現上述這種對特定空間與物件幾近耽溺的眷戀,因此充分運用並轉化它們,使之成為從展覽場址返回電影意象的路標,是他過往影像裝置作品的重要特質。此一作法在「來美術館郊遊」達到顛峰。除了將電影場景情境化,使觀眾宛如置身影片中的密林或廢墟一般的沉浸經驗之外,「來美術館郊遊」更透過不同投映介面和層層樹影的錯落,輔以未被剪入的毛片,形成既與電影影像緊密連結,又與之平行的殊異視覺經驗。這些有著截然不同造形和投映型態的新生影像並非電影文本的附庸,而是在美術館的新場址裡取得獨自生命力的藝術作品。譬如當時展於北師美術館二三樓電梯旁,一片將佈滿壁癌的斑駁牆面幻化成抽象造形肌理的流動影像。又或者展場另一處特寫小康側面的熟睡臉龐,宛如繪畫一般凝結的投影畫面,都是蔡明亮充分運用美術館展呈框架的創作巧思。
然而,上述藉由多重影像投映關係與物象鋪排來「包圍」觀眾的空間佈置策略,到了「無無眠」展卻全數消失,僅剩下美術館原本的大片玻璃窗,和幾乎沒有太多施作的素樸空間。習慣從《是夢》到「來美術館郊遊」這條影像裝置路線的觀眾自然會感到困惑甚至不解。據藝術家自己的說法,他期盼的是讓「影像回到影像」,原本「來美術館郊遊」將空間填滿樹枝的作法,部分是為了克服美術館白天的光線問題;夜間開館的「無無眠」展自然就沒有這種顧慮。(註2)另一合理解釋是保留二樓玻璃帷幕通向館外的開闊視野,那麼《無無眠》中的極緩節奏,就能與窗外捷運所象徵的城市快速步調形成視覺上的對比。倘若如此,「開窗」的考量多少有其必要性。不過前述兩點說法可能都無法真正免除批評者們的疑慮,尚有其他更為充分的原因嗎?我認為關鍵仍必須回到人的「聚集」(gathering)上。
人的看顧與照料
事實上從「來美術館郊遊」起,蔡明亮便大量舉辦各種日常化、通俗化,甚至社區聯誼化的教育活動,充分掌握美術館教育推廣功能所能帶來的連結性與擴散性。(註3)他曾說:「延伸的活動很簡單,就是希望帶觀眾進來,是一種分享的概念,因為過去喜歡我的電影的朋友都不太能分享自己的感受,電影看完了無法感染擴散,但是有趣的活動是可以互相分享傳遞的。」(註4)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他過去舉辦的深夜講堂、故事坊,還是此次「無無眠」展的「夜唱美術館」,這些活動其實才是作為策展人的蔡明亮,親力親為地「caring」他的(未來)觀眾的關鍵時刻,目的都是為了使其影像美學擁有更多與市民生活接軌的可能。正如自《你那邊幾點》(2001)起便養成的親自售票習慣,蔡明亮始終保持他那「一位一位兜售的真實交心」。因此,這些週末小型音樂會或漫談沙龍乍聽之下,固然可能會給人綜藝化或迷眾(cult)化的疑慮,但平心而論,它們恐怕就是著眼不同的族群;期盼原本不常涉足美術館的觀眾、聽眾,有機會在截然不同的空間情境下,與他的影像相遇。這些以人為中心的場合,自然無須繁複的物件或空間佈置,因為活動本身就已具備重新理解其影像美學的契機。
唯一值得提醒的是,「無無眠」展在此終究還是化為一座供既有舊影迷朝聖,或者讓新觀眾學習的藝術電影院。它雖然展出新作,但主要仍是朝向過去而非面對未來;它指向的是已然積累的創作成果,而非引領我們走向影像美學的「域外」。截至目前為止,它最主要的價值仍是作為一個具回顧性質的教育平台,將觀眾帶進蔡明亮的電影世界,一窺其堂奧。於是我們見到的是一位慢下腳步、耐心等候觀眾跟上的蔡明亮,而不再是那位在影像創置路途上不斷超前的孤行者蔡明亮了。這些選擇無謂對錯,只是我們必須意識到,蔡明亮無疑是台灣在「電影進入美術館」議題的領頭羊,因此他的創作走多遠,台灣在這條電影與視覺藝術相互匯流的藝術新範式的探索道路上,就走多遠。倘若如此,如今已有美術館教育平台作為後盾的蔡明亮,理當可以放心實驗、大膽步入無人探索的影像荒漠;駐足在影像放映場所的移置與轉化的思考裡,無疑是有些可惜的。
註1 江凌青,〈就看我怎麼演─《情色空間》中的電影美學脈絡〉,《電影欣賞季刊》,第29卷,第2期,第146輯,頁62-66。
註2 請見王振愷訪談,〈流浪,慢走,美術館—蔡明亮談進入美術館〉,《放映週報》。網址:http://www.funscreen.com.tw/feature.asp?FE_NO=1548(瀏覽時間:2016.04.13)
註3 學者孫松榮曾詳細申論過蔡明亮電影美學裡這種可俗可雅的彈性身段。詳見:〈持續交錯的閃動著:評《來美術館郊遊:蔡明亮大展》的影片展覽〉,「台新ARTalks」網站。網址:http://talks.taishinart.org.tw/juries/ssy/2015013103(瀏覽時間:2016.04.14)
註4 同註2。
Tag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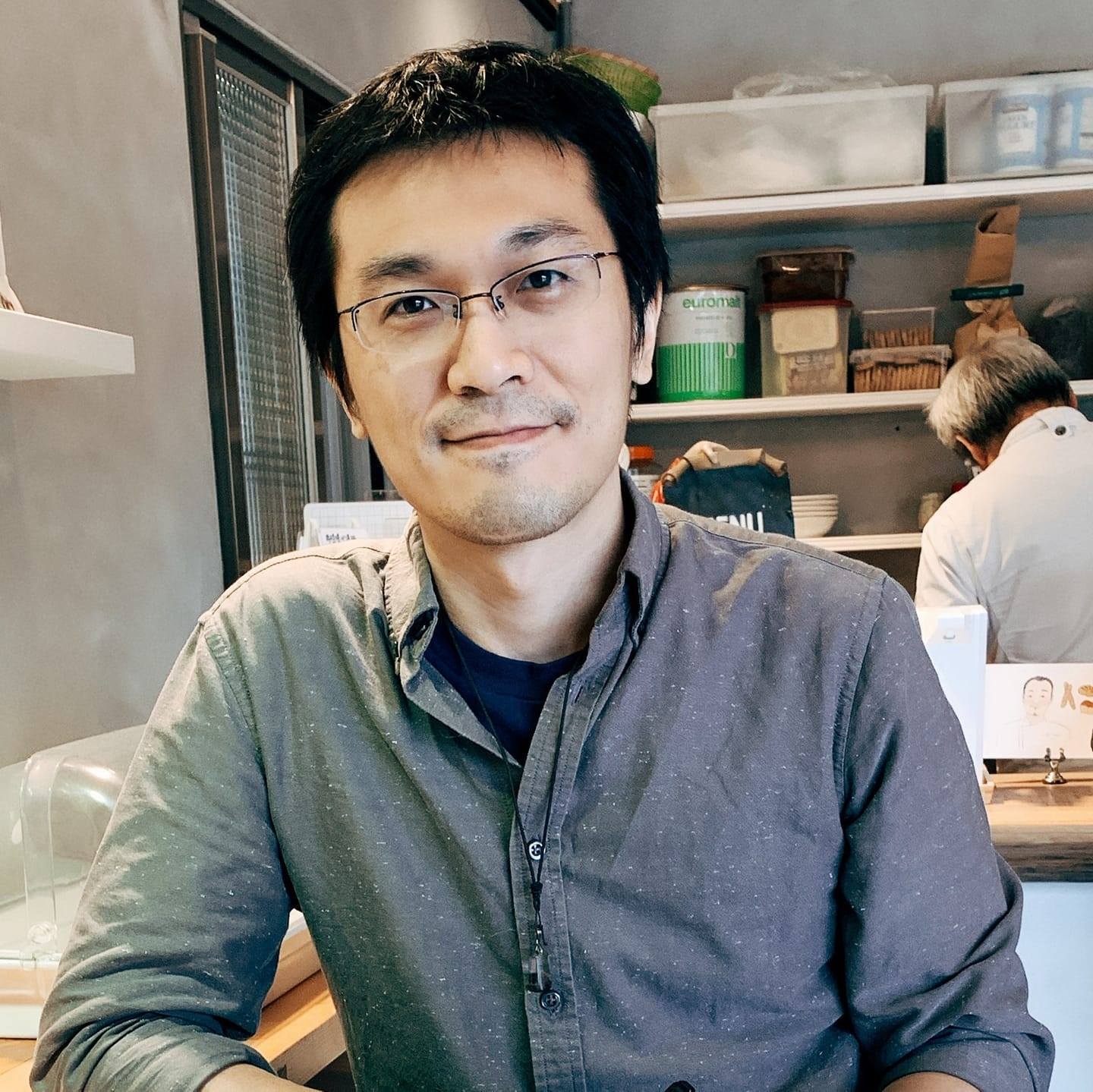 王聖閎( 13篇 )追蹤作者
王聖閎( 13篇 )追蹤作者藝評人,現為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任台新藝術獎提名觀察人(2017, 2018, 2021)。主要研究興趣包括當代錄像、行為表演及身體性創作;關注當代加速度政治下的生命政治課題,聚焦於科層機器對身體行動和耗費模式之影響,並且在此基礎之上,持續反思在地藝術理論的生產與擴延。文章散見於《典藏今藝術》、《藝術家》、《現代美術》,以及台新藝術獎「ARTalks」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