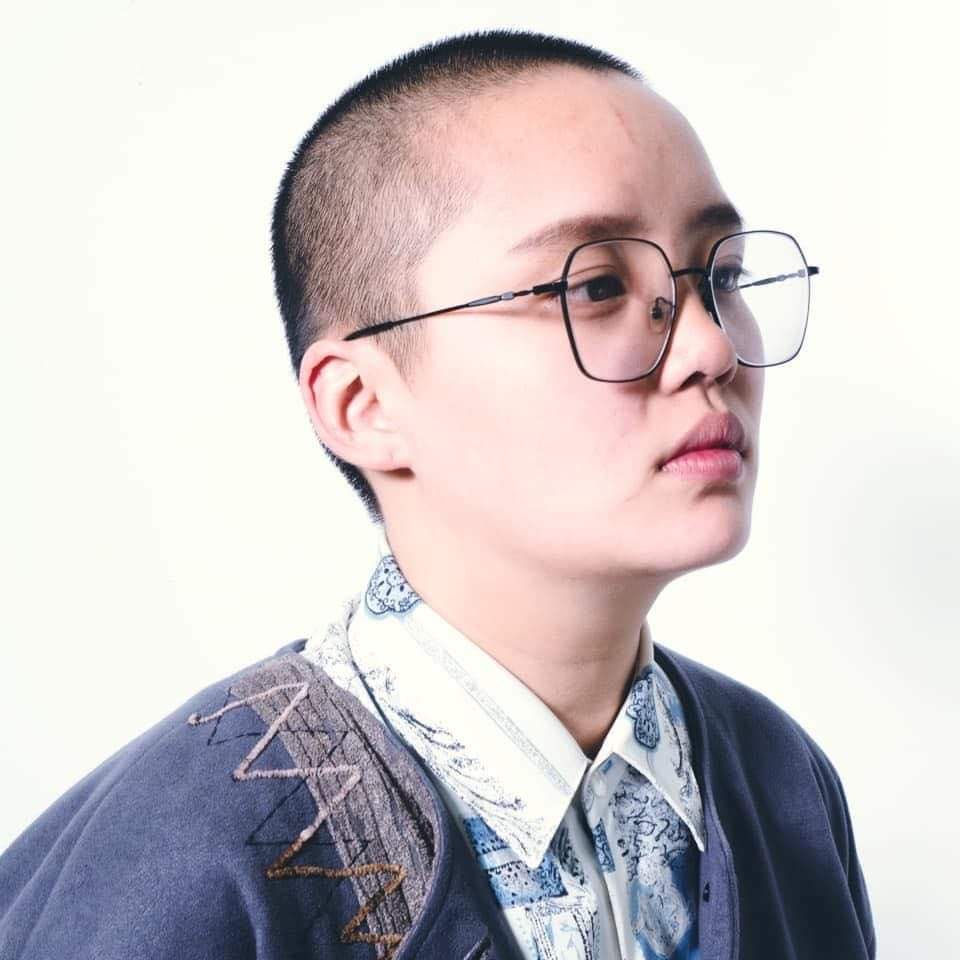當畢展成為形式
當我們走在不斷向前推進的線性時間線上,回望過去的能力,不再僅限於記憶片段的沾黏,更是臆想滋生的場所。這或許是我在收到陳晞邀稿後,有些抗拒打開畢業展覽回憶黑盒子的主因。但在展覽尚未發生的那時間點,我都願意許以它美好的一面,並向它靠近。
以日夜學制聯合舉辦一場符合畢業門檻的展覽,在籌劃、執行面所帶來的分歧、爭執,充滿戲劇張力的場面,我這邊就不多贅述。這篇文章前半部想帶大家回看是什麼因素,讓我們堆疊出對於展覽的想像。

在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簡稱「臺藝大」)舉辦的「空氣草─當代藝術中的展演力」及「大台北當代藝術雙年展─超日常Daily+」這兩場展覽當中的展覽樣貌,讓我和班上幾位同學,感受到展覽所帶出的「共生式」策展機制,以及提供參展藝術家先行對話的平台。讓展覽作品尚未成形時,可通過彼此作品的初步構想,作為啟動展覽未來樣貌的方式;又或是以《翻牆者》這本以展場空間做為主軸所書寫的小說,與創作者作品發想之間彼此互為文本的過程,都讓當時矇懂的我們,彷彿可以藉此窺探當代藝術的一隅。那份衝擊,在我們這屆畢業生中不斷發酵,產生強烈的憧憬,使我們在這場必經漫長溝通與統合的畢業展之中,放入對於展覽的想像。
懷抱著對策劃展覽憧憬的我們,首先以時間、空間的面向進行思考。當時的出發點,是希望能有別於以往的畢展案例,在以成果為導向且快閃的展示中,去挪移出一些縫隙,讓原本在製作作品中容易被忽略的時間線變得可見,也使創作者與空間得以長時間的共處,隨著展出時間與環境變化,產生相對的自然關係。
場地與預算是這個需求面臨到的現實困境。如果以畢籌會折衷所期望的一個月展期,任何校外空間都會形成一筆巨大金額開銷。可轉念一想,為什麼不直接辦在校內呢?然而,當時美術學系畢業門檻的其中一條是校外展覽的要求,透過與從畢製指導教授、美術學系到美術學院的一連串體制科層,接連提出我們對於畢業展覽的想像,讓這些硬性規定不再成為我們想像的阻礙。展期也進而拉長到校方與畢籌會協商的長度,並讓作品的製作(工作狀態)也成為這場展覽的一部分。
延伸閱讀|【給Z世代的藍色時期】當代藝術蹺蹺板:從技術臨摹到思想揣摩的斷裂式教學與其焦慮

時間的拉長,也讓空間之於創作者來說,變成一個需要不停面對的對象。在空間這個面向,畢籌會與有章藝術博物館協調,使用九單藝術實踐空間、北側藝術聚落、臺藝大二校區紙廠等場地。這三個空間中,有些是舊校舍改建或工廠整修後的樣貌,使作品被迫面對展出的場域、外在時間的流動等問題,不再被白盒子空間帶來去地方化、去時間化等條件保護。除上述的場地與展期外,還需將人員組成納入考量,畢業展覽作為各式各樣創作樣貌的集合,策劃時所懷抱的想像,是否為一場徒勞的練習?組織到後期,我自己都開始恍惚了。對原先框架的撼動,真有其必要性嗎?失落感讓我整個人動彈不得。
回看展覽本身與藝術創作者的主體性,該如何彼此兼容?我想這是所有展覽都會面臨到的問題,大至美術館級別的雙年展,小至大學體制裡頭的畢業展覽。以展覽作為號召,讓藝術創作者做出與之互相共生的狀態,是我個人所期望的。可現實是,當面臨一個公共事務時,多種意見彼此摩擦,彼此之間的話語權相近,最終沒有一個能拍板定案的角色在其中。
使起初對展覽的想像,好像成為多餘的步驟,或許以畢業展覽的性質,就該採用具包容性的題目,去囊括多元的作品型態。希望以策展為導向的想像與畢業展覽的現實面,兩者之間反覆拉扯,也讓這場畢業展覽成為模稜兩可的產物。
延伸閱讀|跨出校園或重啟邊界(簡子傑/文)

對組織與策動的反思
畢業展覽所帶來的問題也讓我不禁思考,撇除自己身為參與者的角色,也不論展覽本身與創作主體性之間的平衡。總得來說都是想對現有體制、結構作出回應。在陳晞文章中所提到的「北藝大美術學系碩士班:2022春季開放工作室」也是一個鮮明的例子。學生自發性去運籌的展覽,或許都是在為步入藝術領域進行練習,而在這練習之中的組織意識,與後來我所參與的藝術團體是類似的,都是以組成團塊的方式聚集在一起,避免單打獨鬥的場面,可當這份練習真正放入藝術領域,所帶來的失足感,又是那麼的深刻。
在大學畢業那年,我進入由臺藝大學長組成的「超限游擊」(OGA, Overrun guerrilla act)裡頭,這團體集結著許多我很欣賞的藝術創作者們,然而在團體的運作之中,雖然有著密集的會議討論,彼此之間卻感到生疏。少了些對於藝術的相互激發,朝向投件時間壓力下的工作分配,讓整個團隊籠罩在一個目的導向的氛圍。這讓我對於幾種組織經驗,產生些許反思意識。

以畢業展覽為例,就是以對「展覽」的想像,去驅動彼此作品能開展出的面向,同時拿捏與學院審查之間的矛盾綜合體;而「超限游擊」的組織意識,較偏向爭取在藝術領域中的資源分配。後者在「組織」或是「聚集」,假定出一個作品樣貌,以呼應著主敘事的走向,不再只是自身創作脈絡的延展,而是要符應主辦單位的展望。兩種組織意識的差異,使作品的樣貌,在明確和模糊之中來回踱步,之於藝術創作來說各有利弊。我僅能以個人有限的展覽與藝術團體經驗,去眺望藝術生態的局部樣貌,並在其中試圖取得平衡。
延伸閱讀|【給Z世代的藍色時期】你的教養不是我的教養,學院的藝術養成之術
(責任編輯:陳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