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邊界操作技術
台灣,這座位處在帝國夾縫之間的島嶼,始終經受著來自內部與外部的邊界操作力量之拉扯。向內看,最顯而易見的拉扯即是基於國族認同光譜之差異,劃分出「我族 vs. 他群」的排他力量。又或者,體現在台灣社會面對新住民、外配或移工等族群時,不自覺流露出歧視、冷漠心態的內在他者問題。今年5月,陳界仁領取第12屆AAC藝術中國(Award of Art China)「年度藝術家」獎引發若干質疑與批評,藝術家在返台之後慎重其事地發表了長篇訪談〈一個相信「佛法左派」的藝術家:陳界仁在現實裡的持續創作之路〉(簡稱〈佛法左派〉,註1)。文中,藝術家對批評者的回應方式便是聚焦在內在邊界操作的討論。他嚴詞批判領獎事件的質疑聲浪,正是遂行一種將不同意見者予以外部化的「忠誠檢查」,指其為一種依據統獨政治立場,將人民任意切割為「愛國者/賣國者」的排他性暴力。而在這種切割力量背後,無疑是一架不斷劃定敵我界線,反覆生產「異己」的無情機器。
但另一方面,領獎事件的質疑聲浪並非毫無任何緣由。因為這些聲音主要是著眼於來自外部的邊界操作之力——意即帝國的滲透之力——的深刻反思。中國,如今作為快速進化版本的帝國,同樣發展出各種劃定界線的技術、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管控技術,以及一系列操縱其他政治實體,遂行帝國擴張之欲的「邊界跨越技術」。舉凡宛如科幻影集現實版的「社會信用分數」系統、頻繁的軍機繞台與領空進逼行徑、試圖將台灣主權予以架空弱化、製造「未統先治」假象的「港澳台居民居住證」;又或者,反映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東突厥斯坦)「再教育營」裡浮現的人口監控與壓迫問題,以及在「中非合作論壇峰會」背後呈現出的債務陷阱式外交與殖民思維。簡言之,在貿易戰正熾的新冷戰氛圍下,中國作為意欲與美國分庭抗禮的另一個帝國,其有形無形的邊界操作力量早已昭然若揭,且步步進逼。對於帝國操控意識的揭露和批判,向來是陳界仁藝術語言中極具標誌性的面向。因此會有評論放大檢視其言行,或者揣想中國問題究竟如何在他的帝國批判視野下顯影,也就不足為奇了。

陳界仁《帝國邊界I》。(陳界仁工作室提供)
在回應領獎事件批評言論時,〈佛法左派〉一文就內部邊界操作之力所導致的他者化、外部化問題,有相當完整的論述理據。然而,針對台灣同時也必須經受的另外一種邊界操作之力:意即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式進階版帝國治理技術、越界技術、操縱技術,陳界仁卻是選擇採取直上「全球」格局的論述策略,訴諸「早已滲透、主導、穿透全球每個國家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所造成日趨嚴重的貧富不均等問題」的評議層次。又或者,轉入一種不能言明的隱式話語,倡議其所謂的「點滴工程」,強調必須考量中國內部的複雜性,因此「改變」勢必只能「⋯⋯由點點滴滴的微小行動累積而成,而且不要讓默默從事改變工作的人,增加任何困擾。簡化的說,擺出激進的姿態並不難,難的是如何點點滴滴地改變現實。」(註2)對照藝術家在訪談中所述,能在中國展出的種種不易,這可能便是將其藝術裡的「異議」潛遁進帝國的有效方式。但對於期待藝術家也能就帝國主義的「中國模式」發展提出明確批判的人們來說,這種潛遁語式也可能意味種種基於現實關係之考量,繼而展現出來的自我距離化。
歷史-情感-記憶之限界
誠然,領獎事件背後存在諸多未解癥結有待進一步的論述開展。首先,陳界仁的作品向來鉅細靡遺,無論是為華隆女工姊妹們創造歌唱與舞蹈的「情感共同體」(黃孫權語,註3)、替樂生運動參與者整理出詳盡無比的年表,還是為嫁到台灣的中國新住民蒐羅、記述她們所遭受的歧視經歷;無論創作手法是通過感性的現場重建(廢棄工廠、檔案間、審訊室、機構窗口⋯等),還是凝結藝術家個人生命史的幽微物件(衣物、床墊、地圖、報廢電腦零件⋯等),簡言之,陳界仁的藝術語言總是充滿各種具體的細節。
但我們不難察覺,這些細節往往聚焦在「台灣經驗」上,訴說新自由主義政策下的產業結構轉型,以及勞動力部署的全球遷移所導致的各種殘酷淘汰與「無用的幽靈」(specter of uselessness,註4);又或者,它們總是不斷映射著歷史,特別是舊冷戰時期,美國帝國主義在東亞地緣政治脈絡之中的種種影響痕跡,批判受其扶植的國民黨政權如何藉由黨國教育暨戒嚴體制,徹底扭攪、斧鑿、撕裂一個人的身體和心靈。無論這些細節最終被鍛造成什麼樣的聲響團塊與恍惚魅影,它們不僅形塑出陳界仁的帝國觀,同時也正是其帝國批判視野的「歷史-情感-記憶之限界」。在這條主要是以「美帝」、軍事戒嚴體制、新自由主義掠奪體系作為控訴對象的思想反抗陣線上,帝國主義「中國模式」對台灣同等深邃的模塑刻畫,究竟會被置放在哪裡呢?
近年,陳界仁的創作與言說往往推升至一種宏觀格局的批判語境,直接訴諸跨國資本主義的全球監控和治理,從科技技術到生活技術對每一個個體的暴力形塑。譬如《十二因緣:思考筆記》地下道場景裡反覆出現的監視器攝獵畫面,以及被傳輸線路無情貫穿的空洞身體。嚴格來說,這樣的問題意識不能說毫無任何涵蓋「中國模式」的潛能,只是它更加偏重呈現對人的某種普遍化剝奪、壓迫或異化。因此,希望看到中國的具體治理痕跡也能在此全新創作階段中現身的人們,自然會感到失望。(註5)
回到領獎事件的論爭,在質疑與批評陳界仁的相關言論中,其實有相當大的成分是針對其帝國批判視野之限界而來;台灣當前所面臨的處境,當然可以直上全球金融與科技資本主義的層次,從演算法、大數據資料庫,及後門監控軟體所共構的隱形政體來談。但無論我們議論哪一種攸關台灣未來命運的資本掠奪或操控,中國與美國,恐怕都不會是全然置身事外的旁觀者。最重要的是,當前對於帝國的討論,往往有過於偏重其「資本的權力邏輯」(以資本控制為目標的積累)之分析的弊病,而忽略了回到具體實存的地理空間層次,另一帝國擴張的傳統驅力「領土的權力邏輯」(透過剝奪土地來積累的手段)從來不曾消失。(註6)因此,若要能夠清楚辨析帝國治理體系如何貫穿島嶼內外並展開各種抹消邊界/重劃邊界的激烈角力,我們需要的恰恰是諸多感性經驗的細節,好讓我們不至於描繪出一張去脈絡化的、有所空缺的認知圖景。這恐怕才是質疑聲浪背後,真正透露的共同焦慮。

陳界仁《帝國邊界 II——西方公司》。(陳界仁工作室提供)
無頭者的共同體
承上所述,當前其實有許多針對帝國「邊界跨越技術」的警醒或批判之聲。領獎事件的第二個癥結便出在如何解讀這些想法的問題。而這也是事件之後,實質對話仍難產生的關鍵之一。如果說,將陳界仁的領獎僅僅理解為「收編」,是小看了藝術家言說行動的能動性。那麼同樣的,將台灣內部拒絕帝國滲透的聲音,以及將那些意欲抵抗強權治理進逼的立場「扁平化地」理解為民族國家思維下的忠誠檢查,恐怕也是對台灣內部複雜性的一種簡化與混淆。這是因為,對於(尚未真正到來的)共同體的想望,並不能直接與保守、排外的國族基本教義派劃上等號。事實上,為了持續保有一個讓所有人都能對未來展開相互說服和論辯的多元空間,清理出一條反對帝國單一統治邏輯的共同體思想路線,無論如何都是必要的。
喬治.阿岡本(Giorgio Agamben)曾通過對喬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研究指出,共同體在某個意義上,仰賴的正是共同體的不可能。但也因為願意承認內在的紛雜與歧異,正視「悅納異己」之巨大艱難,共同體的創建工程才可能真正跳脫出對普遍性(universality)的虛假預設,繞過不假思索的排他性暴力。換言之,真正的共同體只能是「那些沒有共同體的人們的共同體。」(註7)沒有共同體之人的聚合,究竟是什麼意思?有一個鮮明無比的意象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那就是巴塔耶曾提出的「無頭者」(Acéphale,註8)概念。但在此,頭顱的闕無不是悲情的「被斬首」,更不具有烏合之眾、群龍「無首」的負面意義;相反的,Acéphale正是以其「無頭而立」的姿態拒絕臣服和奴役,抵抗任何至高神性、君王、獨裁者、寡頭政治由上而下的統御。它既是對「首」的刻意排除,也是對思想教條和無上律令的徹底否定。

喬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曾提出「無頭者」(Acéphale)的重要概念,而翁退.馬頌(André Masson)於1936年為《無頭者》第一期所設計的封面,將Acéphale描繪成一手握著匕首,一手捧著一顆燃燒心臟的形象。
借用這個無頭者意象來引伸與擴延(讀者們或許會想到張照堂1960年代那張著名的無頭者攝影),台灣作為一個原住民、各方移民、流亡者,乃至於遷佔者的聚集之地,在多重帝國邊界操作之力的交錯下,詭譎地陷入一個欲望國家而不可得的無明狀態,只能卡在懸置空間之中等待未來救贖,猶如蘇育賢錄像作品《花山牆》裡的魂身,縱使浴火自焚也盼不到國家主權的到來。在過去,這個島嶼長期被安裝一顆遂行威權體制和黨國教育的虛假頭顱,強迫冠上錯認的身分,即使歷經解嚴後多年,仍未能走出斬去這顆頭顱的陣痛陰影。但至少,如今國家空缺、主權未明的無頭者之姿,尚且保有一個能夠讓不同族群共生,並且積極想像共同體未來的身體空間。雖然這具身體不斷被跨國資本主義從數位演算技術之力到生命治理技術之力所貫穿,但還不至於籠罩在「中國模式」的帝國統治術之下。(註9)因為,一旦帝國的技術官僚體系有意識地與科技的自治力量(註10)形成一種惡性交媾時,兩者交互強化、混合而出的怪物只會更加暴力地挪用任何可取得的監控資料(人口、言論、身體情報的諸資料),遂行資本無限積累擴張的掠奪意志。同時,就跟所有生命系統一樣,牠會想要追求永垂不朽,迴避死亡(政體系統的內在崩潰)並且不斷進化下去,甚至超出帝國的使徒們所能掌控的範圍之外。

蘇育賢《花山牆》。(耿畫廊提供)
此時此刻,台灣還不至於淪為帝國避免自身崩潰死亡而掠食的牲品,但她仍時時深陷在身體感官被麻痺、遮罩,繼而被強權政體再裝設另外一顆虛假頭顱的「去主體性」危機中。據此,盼望與帝國之間保持一定距離、保存對未來共同體的主控權,這些聲音即使也是一種邊界操作,但恐怕是為了與帝國「劃清界線」,撐開一個不受支配的領地。借用〈佛法左派〉裡所倡議的觀點,難道不正是在抵禦治理之爪侵襲的前提下,其所謂的「讓各種『異議者』可以相互學習如何『共生』之地」,才有真正實現的契機嗎?
「能不去做什麼」的抵抗
領獎事件的第三個癥結,是〈佛法左派〉一文裡反覆觸及的當代藝術集體困境。這點,需要回到藝術家的「做」與「不做」來談。在《路徑圖》裡有一幕視覺上極具象徵性的場景,是藝術家安排高雄港碼頭工人駐足在一處裝設有鐵絲網的建物圍牆兩側,以沉默無語的方式傳遞寫有「碼頭工人不會孤單,團結無國界」、「世界就是我們的罷工線」等抗爭標語的畫面。藝術家以影像虛構了一場罷工行動,一條重新召喚歷史的罷工線,讓在地勞動者的身影得以連結上全球勞工運動抗爭史。這種場景的擬構,是他藝術中頗為常見的創作手勢,不僅充分展現影像行動的「潛能」(potentiality),也捕捉了勞動者可以「有所不為」的「非潛能」(im-potentiality)姿態。
在此,「有所不為」並不是姑息、袖手旁觀、鄉愿等負面義的「不作為」,更不是選擇坐看事態惡化的保守心理,而應該從「是不為也,非不能也」的角度理解。換言之,一個人「有能力去做什麼」(如工作和生產),未必總是以能力的施展來彰顯。正如同所有的罷工行動,都是透過勞動者展現她/他「有能力不去做什麼」、刻意「不事生產」來表達抗議。這其實才是人類擁有「潛能」的全部真義,意即同時保有「去做」與「不做」、「去實現」與「不去實現」的兩面性;甚至,判斷一個人是否擁有潛能,應該從她/他是否真正保有了「使自己可以有所不為的能力」來檢驗。唯有充分保留這種「能去做/不去做」的選擇性空間,一個人才能夠說真正擁有了的自由。(註11)
在一篇名為〈論我們能不做什麼〉(On What We Can Not Do)的短文裡,阿岡本指出,當代人之所以貧乏和不自由,真正的原因不是出在被某個巨大無形的宰制結構限制了「能做什麼」的空間,而是剛好相反,是被巧妙地剝奪了「能不去做什麼」的經驗。這是一種盲目,但「⋯⋯不是對自己的能力盲目,而是對自己的無能(incapacities)盲目無知,不是對自己能夠做什麼盲目,而是對自己不能做什麼,或者說,能夠不做什麼盲目。」(註12)換言之,真正不自由的人,是失去「使自己可以有所不為的能力」的人。因為人如果被限制了「能去做什麼」的條件,尚能知道自己該做出抵抗;但是被自己的盲目所蒙蔽,無法再去想像「能不去做什麼」的人,連抵抗的能力都會徹底喪失。
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對於「彈性」、「變動」、「靈活」等價值的迷信即是如此。這些價值不只體現在跨國企業的全球佈局思維,更透過各式非典勞動的條件,徹底內化、植入一位勞動者檢視自身價值的基本準則裡(註13):你應該具備隨時能將過去所學砍掉重練、學習新知的能力,或者隨時可以打包至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與不同背景個性的人一同工作的能力,抑或隨時處在多工、多職、多才的狀態、輕鬆適應斜槓人生的能力。簡言之,所有人都使自己屈從於這種無可違逆的偉大靈活性,因為這是今日資本市場要求每個人都必須具備的首要特質——除了「說不」的能力。
我們不難發現,當代藝術工作者正是最順服於上述價值的勞動者(甚至最以這些價值自居),而當代藝術世界也是這種「彈性成為禁錮枷鎖,變動成為永恆牢籠」之集體困境最極致的展現。因為這個世界有著太多以藝術之名的「非做不可」,使之成為一個即使資源稀缺、人力配置嚴重不足,都依然能自我持存的「供養體系」。(註14)這裡頭,無疑存在一個更細微且不易覺察的權力佈置,讓所有藝術工作者都逐漸失去能夠「有所不為」的餘裕,徹底滾攪在超工作狀態與過量的展演生產循環裡。這隻結構性惡獸的其中一個面目,多年前已在龔卓軍所策劃的「我們是否工作過量?」及其相關的評述討論中被勾勒出輪廓。但牠恐怕永遠不缺繼續壯大的餌食,因為一項殘酷的事實是:藝術工作者幾乎是不會罷工的勞動者(所謂的「藝術罷工」彷彿便是對自己生涯發展的背叛,甚至是扼殺。)藝術體制早就洞悉這點,大至國際雙年展平台,小至學院制度,其中潛藏許多尚待我們嚴肅檢視的生命治理體系,因為它們不僅時時雕塑藝術工作者的藝術生涯,同時,也直接針對其生命與身分本身進行再生產的工程。
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東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gri)曾順著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對生命政治的分析理路說:「生命政治生產的終極核心不是為主體生產客體——如我們一般所理解的商品生產那樣,而是生產主體性本身。」(註15)此言一點也不假。問題是,我們是否還擁有走向這個結構外部或外邊的可能性?抑或,我們只能接受牢牢綁縛在其內部的命運,並且透過嘗試接近龔卓軍所言的「活勞動」狀態(註16),好贖回屬於自己原有的真正潛能/非潛能?
藝術家的身體作為一種積累策略
在〈佛法左派〉一文裡,陳界仁花費不少篇幅自述從1998年以來,他持續陷在一個「弔詭的迴圈」:若不去參加國際性的展覽,在台灣就幾乎沒有出路。但若要持續回應這些展覽的邀約,就必須一直處在拿房子去貸款的惡性循環。為了避免停止創作、藝術生命的死亡,我們看到藝術家同樣捲入一個「非做不可」的瘋狂現實,且確實如文中所言,這是絕大多數台灣藝術家都可能會遭遇到的集體困境。唐娜.哈樂薇(Donna Haraway)曾經精準地指出,身體乃是「一種積累策略」(Body is an accommodation strategy.)。(註17)那麼就陳界仁所描述的「弔詭的迴圈」,我們必須問:是什麼樣的積累策略持續在作用著?姑且先不論背後的「主控者」是誰,至少我們已先看到,這無形的積累策略——作為生命政治的直接生產——以「債」的形式直接作用在藝術家身上,將人深深嵌進一個惡性的資本結構之中。毫無疑問,「弔詭的迴圈」最諷刺的地方不在於使人陷入經濟困頓的處境,而是在於它恰恰是以藝術之名,讓人(自決地)困在一種詭譎的「為生產而生產」狀態裡。
在訪談中,陳界仁反覆強調「該如何發展更有機的資源重分配方式」的思考,例如對於「臨時社群」的設想,以及藉由聚集無力者們,在共同實踐的過程當中孕育人的自我解放契機。不論是自籌經濟獨立的拍片基金,還是藝術家本人與合作者們所形成的情感共同體,無疑都具有良善的信念和情操。但是對照「弔詭的迴圈」的陳述,不得不說,這裡依然存在有待解析的斷裂。
多年前,評論者陳譽仁早在一篇分析《幸福大廈 I》與「臨時社群」的長文裡明確點出,這種經濟獨立的藝術創作計畫可能遠比我們想像中更加「著迷於藝術機制裡的作者特權以及展示文化。」因為這些機制依然是以單一作者之聖像化為驅力,藉此推動資本流動的運作邏輯。所以,即便計畫本身確實抱持著良善的理念(賣作品所得全數投入拍片並給予合理工資),即便它確實在作品內部形成特殊的生產關係與另類的微型經濟,但最後卻依然會「因為過度依賴體制而功虧一匱。」(註18)有些關於陳界仁作品的評論文章,傾向浪漫化臨時社群所具有的「互酬」特質,卻沒能看清楚創作者與藝術作品在資本流動結構之中的真正位置,其實並沒有太大的改變。在此,真正的問題並不是出在領獎事件批評者所說的「分配正義」或累積個人「象徵資本」的問題,而是如我們在「弔詭的迴圈」裡所看到的,連同「成為國際知名藝術家」這件事本身,也已經是這個巨大生命治理計畫的模塑對象,其目的正是為了直接生產藝術家的主體性。

陳界仁《幸福大廈 I》。(陳界仁工作室提供)
理想上,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擁有成為心中嚮往身分的自由。但在「弔詭的迴圈」所呈現的矛盾裡,我們看到反而是「藝術工作者的身分」本身,帶來了極大的不自由(不得不繼續做展覽、不得不進入結構、不得不繼續負債等諸如此類。)此時,人們多半會傾向說「這是自己選擇的路」,卻停止再進一步去推想:滿足了「成為你真正所是的自由」(the freedom to be who you really are),有時卻會以壓制自我轉變的可能性為代價,甚至阻礙了「決定你能流變為何的自由」(the freedom to determine what you can become,註19)。對藝術機制的生命治理體系主控者來說,讓你感受到前一種自由並不妨礙。因為這只是讓你滑入既有身分政治下的主體性生產軌道,在其所規劃的佈局裡獲得預先設定好的身分——例如,成為一位全球國際雙年展與學術型主題展體制底下的優良生產者——但它絕不會讓你接觸後一種自由,因為那意味著讓你重新掌握主體性的生產機制本身。

陳界仁《幸福大廈 I》。(陳界仁工作室提供)
結語:如何重奪身分
先前,龔卓軍藉由「我們是否工作過量?」所展開的討論有一重要貢獻,是指出藝術機制中的真正抵抗,不應該是在「做」與「不做」之間抉擇的零和遊戲;答案不應該是「⋯⋯選擇順服體制遊戲地『做』、甚至得不超常地『做』,像陳界仁般,當個命運上註定要去打破藝術生產常規的圈內人;要不然就只能斷然進行大拒絕式地、整體式地『不做』,還必須像謝德慶一樣,持續ㄍ一ㄥ下去,以維持局外人的純粹高度。」(註20)他透過義大利藝術家弗朗西斯科.馬塔瑞瑟(Francesco Matarrese)與哲學家馬利歐.特隆迪(Mario Tronti)的思考合作,一方面指出「活勞動」與「死勞動」緊密相依的雙重性,唯有透過鬥爭,甚至是反對自己的死勞動,才可能「死中求活」。另一方面,也必須時時提防任何「與資本進行完全整合的勞動形式」,才可能從自己的反面走向結構的真正外邊,找到重新組裝出活勞動的力量。
龔卓軍的解方很值得我們繼續推想下去,但具體方案除了對「異構式的自我組織」的持續想像與實驗,恐怕還必須加入針對主體性生產機制本身的奪還計畫。也就是說,在各種預先給定的主體性生產軌道上,進行「反對自己」式的滑脫是遠遠不夠的;長遠目標還必須放在藝術機制模塑身分與生命的潛在結構,並且在此陣地之上,去探問我們有沒有可能重新奪回這一整套定義「何謂藝術家、藝術工作者」之機制的主導權?在《大同世界》(Commonwealth)中,哈特和奈格里曾給予一個基進建議,指出革命思想不能夠迴避身分政治,反而應該從中學習。甚至,最終應該推向身分政治的消除,他們說:「身分的自我廢止是理解革命政治只能始於身分,而非終於身分的根本原因所在。」(註21)順此思路,猶如工人革命不是消滅「工人」本身,而是消滅將他們定義為工人的身分政治,藝術家與藝術工作者的抵抗(姑且不說是革命)也應該針對將他們定義為「成功藝術家」的生命治理體系暨再生產機器,展開批判性的介入與回應。(註22)
毫無疑問,思考如何重奪身分只是一個開始。面對台灣當代藝術界的集體困境,或許沒有人擁有真正的答案,本文當然也沒有。但我們至少可以嘗試在不同意見交鋒、激盪的過程中,靠向真正能夠施力的起點,而不是直接把作品或相關創作文論當作終點。前提是,藝術的討論——特別是評論實踐——必須抵抗一種「美學覆述」的誘惑。因為這種書寫傾向不僅可能妨礙我們對創作現況提出恰當的詮釋與批評,甚至可能助長一種話語治理力量的聚集。長久以來,正是這些在有意無意之間滋長的覆述誘惑及話語治理,讓評論實踐逐漸喪失其獨立性、陷入沉默,同時也讓我們環境裡的藝術思想步履蹣跚,遲遲難以推進。這才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真正危機。

陳界仁《幸福大廈 I》。(陳界仁工作室提供)
註1 秦雅君採訪與整理,〈一個相信「佛法左派」的藝術家:陳界仁在現實裡的持續創作之路〉,《典藏ARTouch.com》,2018.06.29。(2018.10.09節錄)
註2 同註1。
註3 黃孫權,〈陳界仁作品中的情感技術〉,《典藏.今藝術》,2017.12。(2018.10.05節錄)
註2 同註1。
註3 黃孫權,〈陳界仁作品中的情感技術〉,《典藏.今藝術》,2017.12。(2018.10.05節錄)
註4 Richard Sennett, The Culture of the New Capitalism,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83-130, 2006.
註5 譬如,中國藝評人卞卡那篇因為未能詳查藝術家言論的文脈時序,致使陳界仁工作室嚴詞抗議、要求更正的文章,與其說是「污衊」,不如說是愛之深的殷切盼望;期待藝術家能以他有距離的批判位置,讓中國社會的迫切問題也有機會浮現在其帝國批判視野中。
註6 誠如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提醒,這兩套邏輯有著相互糾纏,甚至相互矛盾的複雜關係,僅從其中一種來理解當代的帝國恐怕都會有盲點。詳見: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著,王志弘、王玥民、徐苔玲合譯,《新帝國主義》(The New Imperialism),台北:群學,頁23-67,2008。
註7 Giorgio Agamben, Bataille et le paradoxe de la souveraineté, Liberté, vol. 38, n°3, (225), pp.87-95, 1996.
註8 Acéphale(無頭之人)乃是喬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同時也是他和幾個友人共同締結的秘密社團,以及團體所發行之刊物的正式名稱。翁退.馬頌(André Masson)於1936年為《無頭者》第一期所設計的封面,將Acéphale描繪成一手握著匕首,一手捧著一顆燃燒心臟的形象。詳見Georges Bataille, The Sacred Conspiracy’ in Vision of Excess: Selected Writing 1927-1939,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 178-181, 1993. 另見Georges Bataille, ed., Encyclopaedia Acephalica: Comprising the Critical Dictionary & Related Texts, London: Atlas Press, pp. 12-17, 1995.
註9 卞卡,〈中國的40年造景:帝國統治術〉,《典藏ARTouch.com》。(2018.10.10節錄)
註10 這裡是指將「科技」視為一種能夠自我強化甚至進化的系統,而非純粹的物、硬體或工具。同時,隨著機械與演算系統環環相扣的訊息交流與反饋,我們應當正視它會產生出自治的驅力和自主的發展軌道。因此,人類社會已經走到必須放棄「科技的整體僅僅是無生命之物,沒有人類它就不存在或沒有意義」這樣的想法。不少論者都有關於科技自主性的討論,例如凱文.凱利(Kevin Kelly)提出「科技體」(technium)的概念。不過凱利的論點仍有揮之不去的科技樂觀主義陰影,特別是將科技體與當代帝國進化模式放在一起思考時,這個缺點會更加明顯。詳見:凱文.凱利(Kevin Kelly)著,嚴麗娟譯,《科技想要什麼?》(What Technology Wants ?),台北:貓頭鷹出版社,頁19-36、280-356,2012。
註11 Giorgio Agamben, ‘On Potentiality,’ Potentialities: Collected Essays in Philosoph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81-183, 2000.
註5 譬如,中國藝評人卞卡那篇因為未能詳查藝術家言論的文脈時序,致使陳界仁工作室嚴詞抗議、要求更正的文章,與其說是「污衊」,不如說是愛之深的殷切盼望;期待藝術家能以他有距離的批判位置,讓中國社會的迫切問題也有機會浮現在其帝國批判視野中。
註6 誠如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提醒,這兩套邏輯有著相互糾纏,甚至相互矛盾的複雜關係,僅從其中一種來理解當代的帝國恐怕都會有盲點。詳見: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著,王志弘、王玥民、徐苔玲合譯,《新帝國主義》(The New Imperialism),台北:群學,頁23-67,2008。
註7 Giorgio Agamben, Bataille et le paradoxe de la souveraineté, Liberté, vol. 38, n°3, (225), pp.87-95, 1996.
註8 Acéphale(無頭之人)乃是喬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同時也是他和幾個友人共同締結的秘密社團,以及團體所發行之刊物的正式名稱。翁退.馬頌(André Masson)於1936年為《無頭者》第一期所設計的封面,將Acéphale描繪成一手握著匕首,一手捧著一顆燃燒心臟的形象。詳見Georges Bataille, The Sacred Conspiracy’ in Vision of Excess: Selected Writing 1927-1939,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 178-181, 1993. 另見Georges Bataille, ed., Encyclopaedia Acephalica: Comprising the Critical Dictionary & Related Texts, London: Atlas Press, pp. 12-17, 1995.
註9 卞卡,〈中國的40年造景:帝國統治術〉,《典藏ARTouch.com》。(2018.10.10節錄)
註10 這裡是指將「科技」視為一種能夠自我強化甚至進化的系統,而非純粹的物、硬體或工具。同時,隨著機械與演算系統環環相扣的訊息交流與反饋,我們應當正視它會產生出自治的驅力和自主的發展軌道。因此,人類社會已經走到必須放棄「科技的整體僅僅是無生命之物,沒有人類它就不存在或沒有意義」這樣的想法。不少論者都有關於科技自主性的討論,例如凱文.凱利(Kevin Kelly)提出「科技體」(technium)的概念。不過凱利的論點仍有揮之不去的科技樂觀主義陰影,特別是將科技體與當代帝國進化模式放在一起思考時,這個缺點會更加明顯。詳見:凱文.凱利(Kevin Kelly)著,嚴麗娟譯,《科技想要什麼?》(What Technology Wants ?),台北:貓頭鷹出版社,頁19-36、280-356,2012。
註11 Giorgio Agamben, ‘On Potentiality,’ Potentialities: Collected Essays in Philosoph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81-183, 2000.
註12 Giorgio Agamben, 2010, ‘On What We Can Not Do,’ Nuditie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4, 2010.
註13 Richard Sennett, ibid., pp.122-130.
註14 關於這種「藝術愛戀式的供養體系」和藝術勞動條件的當代困境,請參見拙文:〈供養的體系: 從藝術圈中間層工作的消失談起〉,《典藏.今藝術》第277期,頁116-119,2015.10。
註15 粗體為筆者所加。詳見: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Commonwealth,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X, 2009.
註16 龔卓軍,〈超工作.活勞動——一個現代主義美學外邊的計畫〉,《我們是否工作過量I:工作手冊》,台北:誠品,頁24,2013。
註17 Donna Haraway and David Harvey, Nature Politics and Possibilities A Debate and Discussion with David Harvey and Donna Harawa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3: 510, 1995.
註13 Richard Sennett, ibid., pp.122-130.
註14 關於這種「藝術愛戀式的供養體系」和藝術勞動條件的當代困境,請參見拙文:〈供養的體系: 從藝術圈中間層工作的消失談起〉,《典藏.今藝術》第277期,頁116-119,2015.10。
註15 粗體為筆者所加。詳見: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Commonwealth,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X, 2009.
註16 龔卓軍,〈超工作.活勞動——一個現代主義美學外邊的計畫〉,《我們是否工作過量I:工作手冊》,台北:誠品,頁24,2013。
註17 Donna Haraway and David Harvey, Nature Politics and Possibilities A Debate and Discussion with David Harvey and Donna Harawa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3: 510, 1995.
註18 陳譽仁,〈被遮蔽的藝術機制:陳界仁的《幸福大廈 I》與「臨時社群」〉,2013。
註19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ibid., p.331.
註20 龔卓軍,〈超工作.活勞動〉,頁19。
註21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ibid., p.332.
註22 必須特別指出的是,廢止身分政治遠遠不是終極答案,且如同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批評,在沒有提供具體策略和替代方案的前提下,輕易取消社會結構既有的層級秩序是很有問題的。同時,任何一個與地方和區域相關的地理認同以及本土認同,都有其生成的自然形式。這點也必須被我們考慮進去。詳見:David Harvey, ‘Commonwealth: An Exchange’ Artforum 48: 3 (Nov 2009): 210-221.
註19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ibid., p.331.
註20 龔卓軍,〈超工作.活勞動〉,頁19。
註21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ibid., p.332.
註22 必須特別指出的是,廢止身分政治遠遠不是終極答案,且如同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批評,在沒有提供具體策略和替代方案的前提下,輕易取消社會結構既有的層級秩序是很有問題的。同時,任何一個與地方和區域相關的地理認同以及本土認同,都有其生成的自然形式。這點也必須被我們考慮進去。詳見:David Harvey, ‘Commonwealth: An Exchange’ Artforum 48: 3 (Nov 2009): 210-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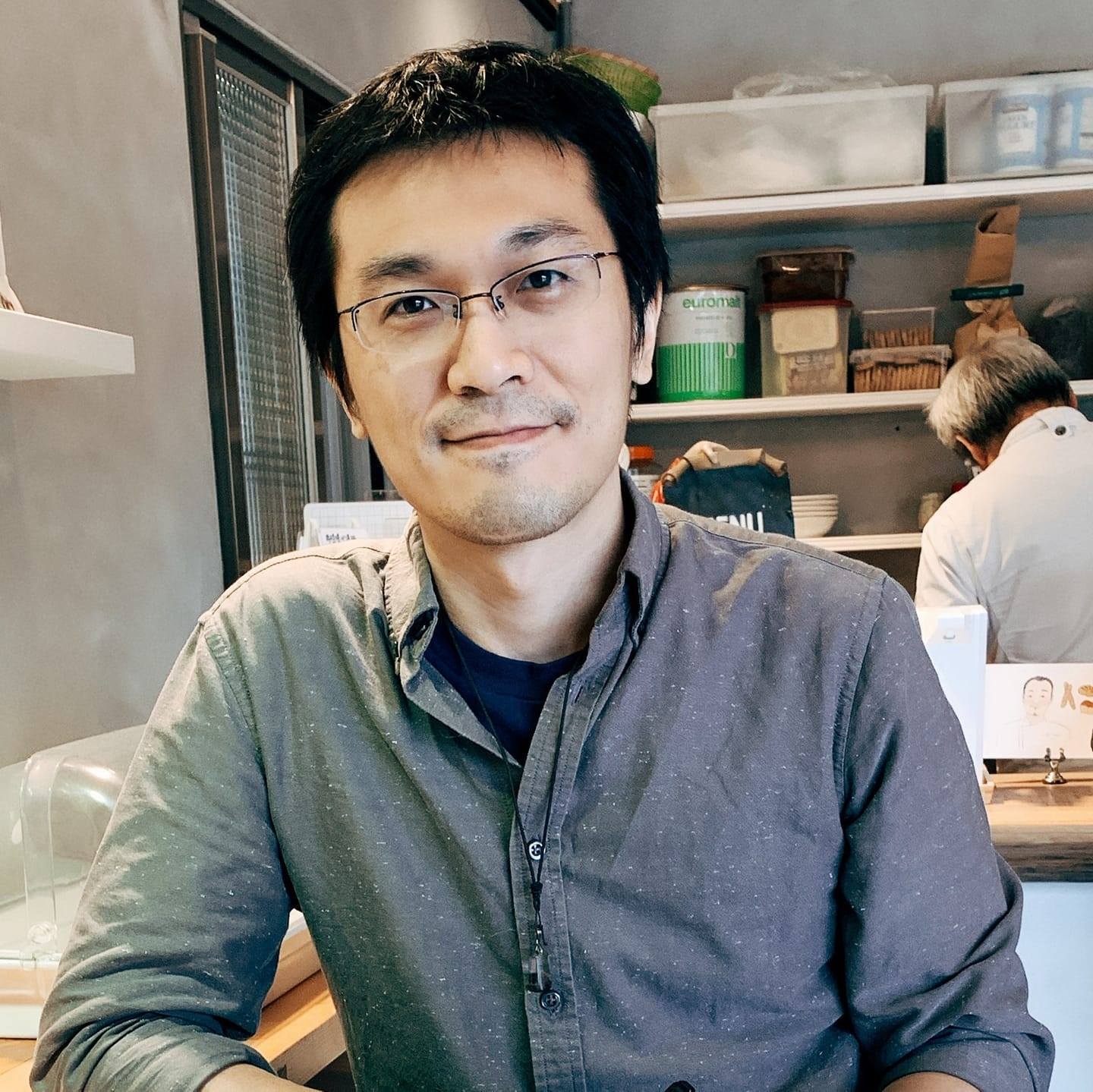 王聖閎( 13篇 )追蹤作者
王聖閎( 13篇 )追蹤作者藝評人,現為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任台新藝術獎提名觀察人(2017, 2018, 2021)。主要研究興趣包括當代錄像、行為表演及身體性創作;關注當代加速度政治下的生命政治課題,聚焦於科層機器對身體行動和耗費模式之影響,並且在此基礎之上,持續反思在地藝術理論的生產與擴延。文章散見於《典藏今藝術》、《藝術家》、《現代美術》,以及台新藝術獎「ARTalks」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