趴伏的素描者
高俊宏複雜多面、有如歧路花園一般的「創作–行動–書寫」體系,本身是一張與死蔭的空間、無主的孤魂、山野荒徑、歷史空缺碎片交換出來的生命輿圖。其軌跡既是精神結構層次的,也是地誌書寫層次的;時而猶豫、時而堅定,且毫不畏懼躊躇再躊躇的迷失漫走,猶如一張歷經反覆的塗抹修改,不停以大量不確定的線條去圈畫、去勾勒,最終形象輪廓才有辦法稍稍浮顯的素描稿。
以「素描」形容他的藝術,不單單是因為自「廢墟影像晶體計畫」以來,又或者在蔡明亮作品《玄奘》中,那位手執炭筆佝僂著、趴伏著的素描者,已成為高俊宏最鮮明的外顯形象之一,更是因為「素描」其實正是他當前實踐體系裡最為核心的一種基本方法。只是在此,「素描」之於他的方法論意義,遠遠不是純美術脈絡下的眼、手、心共同運作,不是侷限於紙與筆之間的肢體運動軌跡探索,而是一種同時兼具「抗辯」與「還原」意味的自我重構。如其所說,乃是一種「撿回來」的動作(註1);是自1990年代以降學院所標舉的現代主義暨觀念藝術框架中脫出,重新撿拾並翻掘自己腳下的思想土壤,讓創作得以獲得安置的一種反身性行動。簡言之,高俊宏近年以大量的圖像游擊、入山調查、故事採摘、理論書寫所勾勒出的「素描」之路,是一場同時在思想戰場及實踐戰場上都進行大規模清整的自我搏鬥。
正因為有上述這層認知,我們是否能以尋常的展覽評判方式面對高俊宏的個展「棄路:一位創作者的地理政治之用」(簡稱「棄路」展),甚至,能否以一般意義的「藝術家」來評判他,恐怕都值得斟酌再三。儘管「棄路」展頗有一次完整呈現其創作軌跡的意圖,而高俊宏也確實具有在畫廊空間裡凝練出高強度感覺團塊的空間部署能力,但愈是細讀他在展場裡所提供的新舊書稿、地圖、筆記、影像及文件,就愈容易察覺,這位藝術家所創造的真正實踐力量總是「在他方」,意即那些通過其行動踏查而捲起的層層意念與漣漪。

「大豹:溫帶的邊界」系列作品於展覽現場。圖│高俊宏.亞洲當代藝術空間
相互寫入彼此生命的「織」
但這並不是說,「棄路」展中作品的佈局配置欠缺引人入勝之處,而是說,這檔展覽在脈絡上的完整呈現,反而更清楚地揭露一種非得透過政治的、歷史的、文學的、田野的,最後才是藝術的綜合性「知識–行動」網絡,才有辦法大致圈圍出的龐大問題意識疆域。而現行的文件檔案形式,已難以承載如此豐沛的思想能量—甚至他大量書寫、研究的出版著作也僅能呈現部分的面貌。就此而言,高俊宏繁複的創作體系其實蘊含一種幽微的未來性,指向某種尚未到來的藝術表達形式。而他現在透過「棄路」展呈獻給我們的「成果」,毋寧說是既有的表達媒介由於無法含納其高張飽滿的實踐動能,因而爆裂破碎的劇烈悶響。
所以,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從「棄路」展向外擴散、折射而出的種種路徑?而其既屬於自我技術學,亦屬於檔案化(archiving)實踐的核心關懷,又該如何理解?此次展出的新作「大豹:溫帶的邊界」系列或可讀出一些端倪。「大豹社事件」背後的未明歷史,是高俊宏近年奮力追索的踏查重心。他不僅深入考掘日治時期,日本政府在強硬的理蕃政策下,以優勢武力侵壓泰雅族大豹社領域的「樟腦戰爭」始末;透過探訪大豹社總頭目瓦旦.燮促(Watan Shetsu)的後代,追憶其祖父、父執輩命運多舛的事蹟。最後,更實際走訪「五年理蕃」時期的隘勇所、忠魂碑遺跡,反覆描摹隘勇線上的諸多漫漶山徑。這些必須銜接帝國侵略史、民間資本移轉歷程,乃至於山林環境測繪的龐大知識組構工程,不僅穿越古戰場遺址所劃定的島嶼內部邊界,更是徹徹底底溢出展場空間所能承載的視覺邊界。
這件作品的亮點之一,是展呈在一旁的延伸錄像《大豹:線》。高俊宏將泰雅族婦女皆會學習的〈織布歌〉(Uyas Tminun)吟唱畫面,與一位日兵針對林中防衛堡壘系統設置的口述畫面交錯播映。細究這兩者的話語,都是圍繞著「線」的概念而展開:前者是在泰雅族的物質文化與技藝脈絡下,對於「捻線」、「理線」等方法的默會傳承。而後者則是戰爭技術視角下,對於防衛線和轉進路線的反覆推敲。如此影像結構上的穿插,不僅是「線」的概念交會,同時也象徵性地「織」出整場戰役中,兩造截然不同的生命敘事平面。我想起悠蘭.多又(Yulan Toyuw)在《泰雅織影》裡,曾指出泰雅族語裡「織」(T’minun)的概念,是與敘說人的一生、人之命運的話語緊密相連的。譬如說人的好運,會說是泰雅族至高的屬靈存在Utux織得好;反之,則說是Utux織壞了。因此「織」不只是外顯的文化行為,更有能否善盡泰雅族人責任,進而最終「回到祖靈所在地」的意涵。(註2)簡言之,在泰雅文化裡,「織」並不只有物質文化層次的意義,更蘊含著從「物」的技藝體系向上連結至人的生命觀、時間觀,乃至於宇宙觀的一整套表達系統。

《博愛》系列作品於展覽現場。圖│高俊宏.亞洲當代藝術空間
若以泰雅文化的「織」作為概念引擎,來看待高俊宏近年描摹出的精神地理素描之路,以及這種以藝術行動為核心所發動的超大型「知識–行動」踏查計畫,那麼,蘊藏在其創作體系中的田野觀、檔案觀就有一個初解:意即,藝術家的實踐驅力絕非一種不假思索的紀錄/紀實,也絕不只是從現代性的廢墟中搶救出什麼;毋寧說,無論藝術家向過去考掘什麼,都是一種足以上升至擾動命運、重新編織生命敘事強度的實踐。一方面,他不斷地「讓生」,使歷史場景裡的惡夢與遊魂藉其書寫、影像,以及身體復活。另一方面,因為與千百個無名眾生長時延的交會,其穿越島嶼荒徑的藝術行動漸次滑入一種不停與「非我」相遇的生命政治軌道,繼而反向地重構了他自己的感覺與身體—這當然是一種「織」的過程,是藝術家與其敘說對象、考現對象「相互寫入彼此生命」的一段深刻交往。
以炭筆為眼,以跟隨為方法
對任何一位評論者而言,像高俊宏這樣行動與思想能量皆豐、且能夠折射出多種實踐方略的藝術家,無疑都是一大挑戰。龔卓軍曾提議,一種可行的評論方法是直接跟著他入山、走入荒野、踏足失能空間,在過程中嘗試與其一同調整與改變。據此,評論必須是一種「漂泊的行動」。(註3)這讓我想起羅獨秀(Alain Brossat)在《傅科:危險哲學家》裡也曾提及,當代哲學家研究的其中一種研究方法正是「跟著他」(avec lui),而這能讓人在研究路上充分感受一股源源不絕的激盪與鼓舞力量。(註4)顯然,在摸索藝術這迢迢路上,道理也是相通的。但以跟隨為方法,並不是在說高俊宏的創作帶有什麼先知色彩,而是說他的「織」其實已是一種網絡式的鏈結與邀約。自「廢墟影像晶體計畫」開始,他的實踐方略已從不斷入山、披荊斬棘在棄路上的「獨行」,轉變成一種活勞動能夠相互匯聚的「網」,足以吸引不同領域研究者、評論者,甚至是空間經營者同行相伴。於其中,彼此各異的研究動機、批評意識皆能共享交流,形成一個高度活性化的交換平台,並且揭示一個帶有「共活」精神的藝術實踐共同體想像。

高俊宏∣兩個1984 單頻道有聲錄像 13”44″ 2014 圖│高俊宏.亞洲當代藝術空間
高俊宏自己其實也是諸多無名歷史之魂的跟隨者。而他的精神地理素描之路,則是在近乎土法煉鋼式的摸索之中,找出與他人、與世界交往的全新根基。正因為它是如此劇烈地對自我、對既有藝術知識框架展開種種卡夫卡式的扭攪、拆解及重組,我以為,展場裡的美學化物件陳列,抑或某種憂鬱氛圍籠罩的幽靈影像塑造,應是此素描之路最不關心的事。這並不是說,展呈空間部署或者殊異感性的開發不重要,而是說「棄路」的另一層延伸義,其實是藉由嶄新的實踐方略,對創作舊路、老路的徹底揚棄。猶如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在《盲人的回憶》(Memoirs of the Blind)裡對「Drawing」一詞的延伸闡釋:除了「描繪」之外,亦帶有向前摸索,去調查、審視、探勘之意,就像盲人將其雙手伸入未知視域一般,是讓身體的觸覺走在觀看的視覺之前。(註5)
高俊宏正是以這樣的姿態,反覆穿梭在東亞現代性的破碎地圖之間。他用以描摹廢棄營區、礦坑、軍事據點或山稜線的炭筆,就是他探向歷史盲域的手。儘管這般操作極可能導向各種迷失與蹉跎,但他以退為進的「棄路」告訴我們,唯有以這支筆去反覆碰觸、塗抹、書寫及描繪,甚至直到這支筆的前端瞪出一顆宛若獨眼巨人般的「指尖之眼」,我們才可能真正在歷史山林的最黑暗處,發現帶有自我救贖之力的未來幽光。
註1 轉引自林怡秀,〈你如何命名那些尚未尋找到的東西〉,收錄於高俊宏著,《陀螺:創作與讓生》,新北市:遠足文化,2015,頁88。
註2 悠蘭.多又著,《泰雅織影》,新北市:稻鄉出版社,2004,頁148-149。另見:小島由道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泰雅族》,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6,頁40。 關於泰雅族將「織」與命運相連的語言觀,承蒙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陳文德先生慷慨分享研究觀點並提供延伸的參考文獻,特此致謝。
註3 詳見2016臺南藝術節─專題座談「種藝.眾議:關於評論—評論不是什麼?」紀錄。轉載於Artalks網站◎talks.taishinart.org.tw/event/talks/2016060802(2017.09.01瀏覽)
註4 羅獨秀(Alain Brossat)著,羅惠珍譯,《傅科:危險哲學家》,台北:麥田,2012,頁9。
註5 Jacques Derrida, translated by Pascale-Anne Brault and Michael Naas, Memoirs of the Blind: The Self-Portrait and Other Rui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pp. 3-9.
Tag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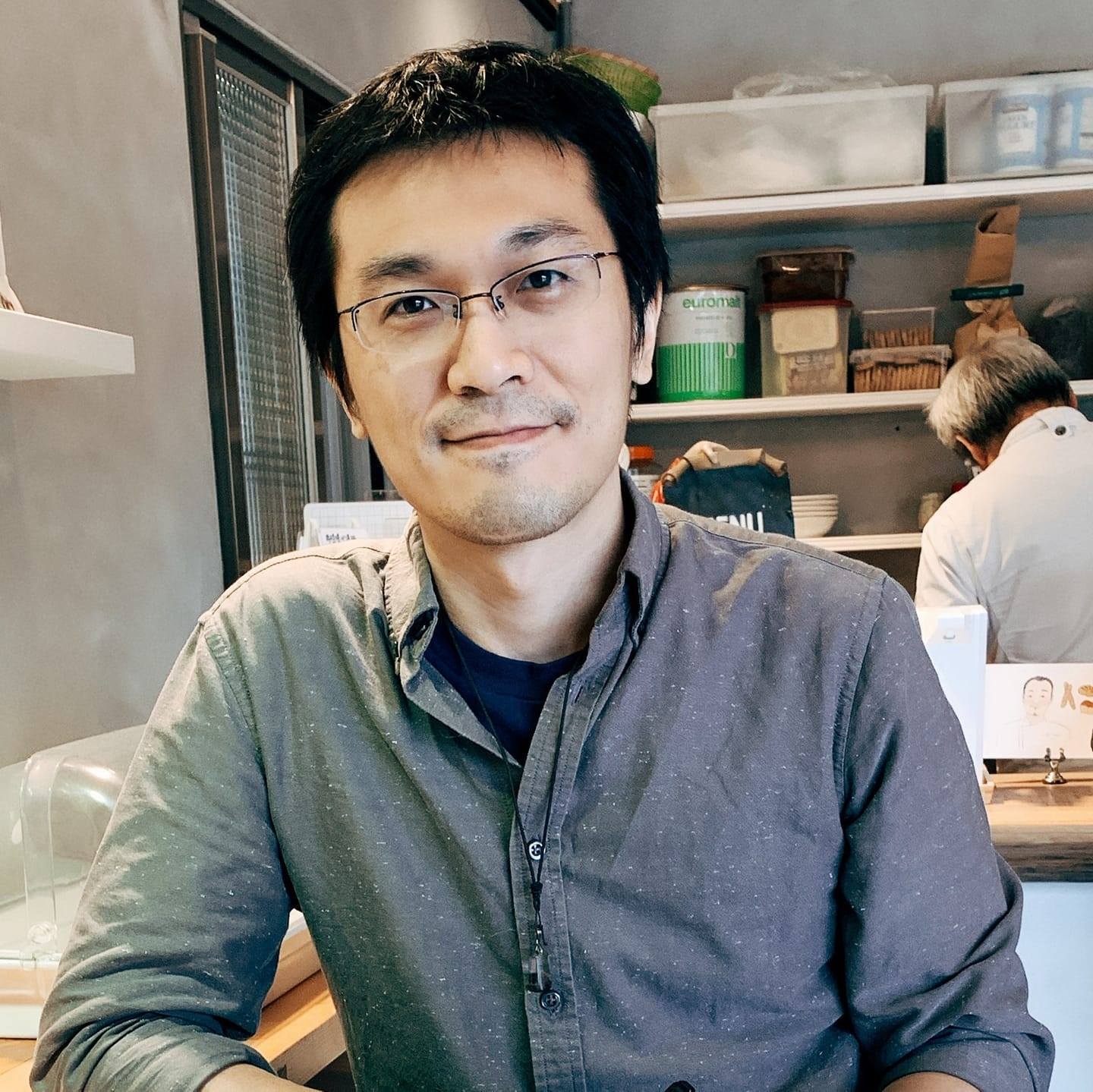 王聖閎( 13篇 )追蹤作者
王聖閎( 13篇 )追蹤作者藝評人,現為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任台新藝術獎提名觀察人(2017, 2018, 2021)。主要研究興趣包括當代錄像、行為表演及身體性創作;關注當代加速度政治下的生命政治課題,聚焦於科層機器對身體行動和耗費模式之影響,並且在此基礎之上,持續反思在地藝術理論的生產與擴延。文章散見於《典藏今藝術》、《藝術家》、《現代美術》,以及台新藝術獎「ARTalks」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