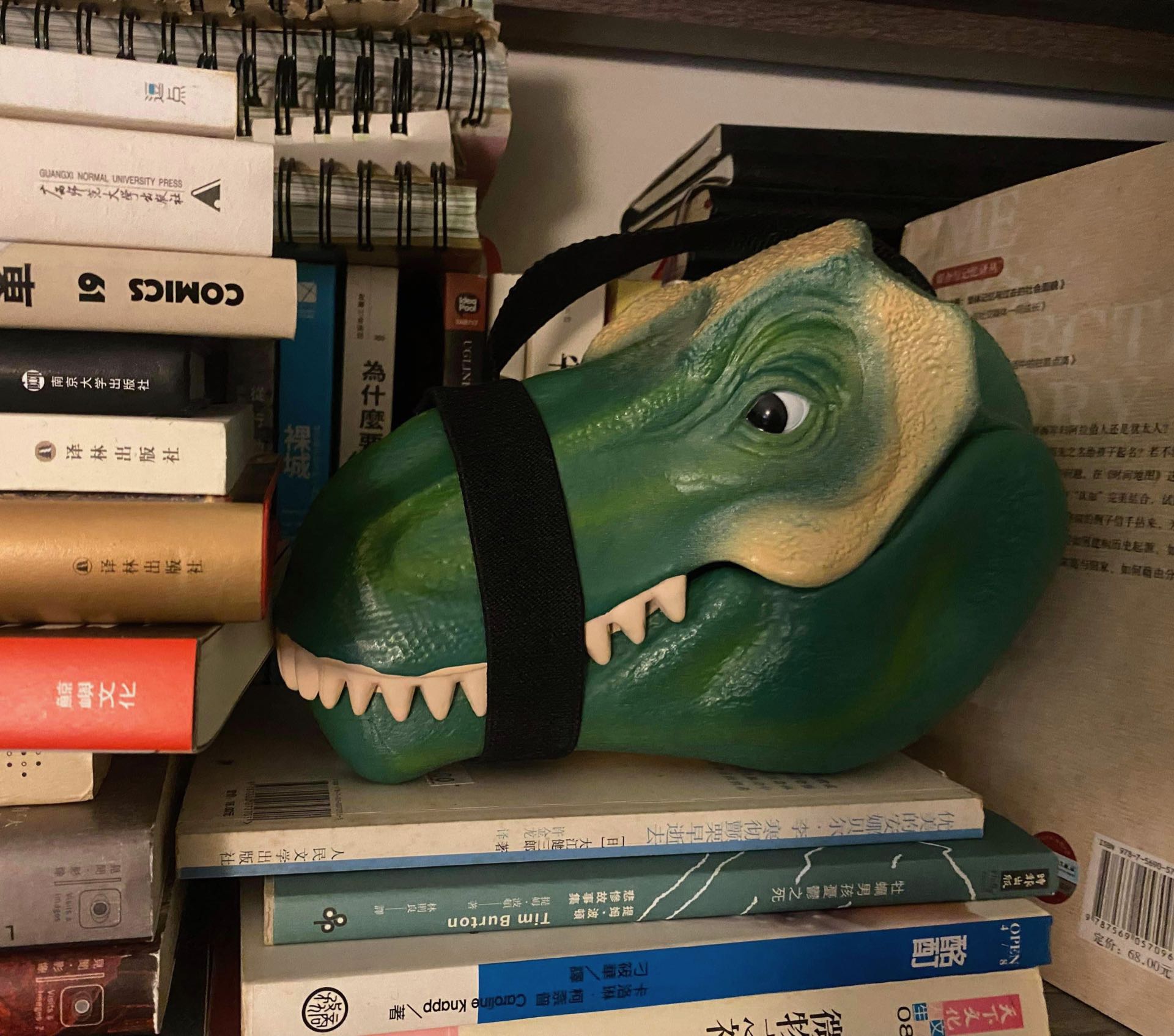2020年底,陳界仁在劉永晧策劃的「EX!T10第十屆台灣國際實驗媒體藝術展」展出名為《再現空白》的電影表演,以過去由陳界仁、邵懿德、馬西宇等人所組成的團體「奶.精儀式」的實驗電影精神作為回溯,展現與當時衝撞、前衛的時代感截然不同的再現。而「Re:Play 操/演現場」(以下簡稱「Re:Play」)三位策展人中王柏偉所負責的區塊以「漫長的90年代」作為主要時間軸,展出高俊宏、姚瑞中、鄭志忠、陳明才、田啟元等人的檔案紀錄,這些狂烈的藝術實驗先行者,在急欲尋找主體性的年代,分別延展出關於城市、行為、劇場或身體種種議題。而這兩檔去年末的展覽命題皆具有變異的時間感,「再現空白」與「漫長的90年代」(註1)等字眼意味著時間的變形,從流動的狀態復返某種不存在的狀態或時間點、本應前進的軸線無限拉長成為一種懸欠,彷彿時至當下,也僅是解嚴以降的一個小小逗點,革命尚未成功、事件尚未完結、行者依舊在路上,但下一世代已到眼前,不得不面對,所有的歷史之痛產生理解與感知的落差,陳界仁與高俊宏亦慢慢另闢關於藝術之於社會的行動模式。


從「反」到「非」 高俊宏藝術與行動的變形記
《陀螺》一書中,高俊宏在〈一創作就矛盾:晚近二十年台灣藝術身體徵候〉的第一句話即引用了謝林(Schelling)所說:「開始是隨著否定而開始的東西的否定。」(註2)來形容1990年代以降藝術創作乃至生存主體的貧乏感,從抗拒戒嚴與黨國到抗拒引渡西方前衛藝術的抽象資本。而從他個人創作脈絡來看,「Re:Play」所回顧的1990年末至2000年初高俊宏的行為藝術可將「社會化無聊」系列中的《美玩美》視為代表之一,為期一週吃進報紙與水果咀嚼,然後再吐出,「吐出」這個動作隱含著拒斥報紙所蘊涵的意識形態、資訊供給、論述建構……等等,但在吐出的同時連帶將產於土地的、自然的水果也一併吐出,彷彿藝術家的身體作為學院知識體系、中產階級秩序化的載體,他一再以身體的消耗及反覆作為一種反抗者的姿態。

而2007年之後他走進廢墟創作,2013年於亞洲藝術雙年展展出《廢墟影像晶體計畫:十個場景》,創作過程中在走訪宜蘭一處日治時期軍事廢墟之際,因緣際會認識了前台籍神風特攻隊隊員張正光,就高俊宏的說法是一個「被舊帝國搞死的人」(而他自己是被新帝國搞死的人,註3),他的關注對象在此從因國家權力迫使失能的「場域」轉移至「人」的身上,並於2015年完成「群島藝術三面鏡」系列書寫《小說》、《諸眾》、《陀螺》,除了張正光外並納進東亞各地如日本、韓國、香港、武漢以及台灣本土的藝術佔領行動,在此時「社群」的觀念亦成為高俊宏重要的創作脈絡之一,他認為:「即便兩個人也能成為社群,而對『社群』的思考是超越佔領的。」(註4)高俊宏的書寫對體制批判、藝術框架的建構力道依舊,但對於介入社會的成功與否已非必須達標的業績,社群創造成為另一個重要主軸。而在《小說》前言中他以「假小說」形容這本「不像小說的小說」(註5),介於當代藝術所關照的問題意識,卻又避免墜入西方經驗的當代性中;同時採用可考據的時代背景,卻在資料極度匱乏狀態下,夾雜虛構的人物事件;更進一步說是虛構又融入大量「我」所踏查的史地資料,行動融入紀錄的、虛構的「假小說」敘事,將以往「非虛構」的行為藝術乃至廢墟系列作品原具有高度明確反抗主體的藝術行為/行動,蒙上一層寫實與反抗性以外的感知脈絡。

接著2016年台北雙年展展出的《博愛》,融合了失能空間(海山煤礦、博愛市場、台汽客運、安康接待室)實景拍攝、當事人現身說法、表演者的肢體演繹與朗讀、藝術家手繪、空照衛星圖、虛構敘事,在虛實向度之間擺盪的《博愛》既以「非虛構」的寫實批判精神為旨,但又在敘事之間嫁接像是高母敘述父親被日軍徵兵的虛構情節、朗讀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或是像是遠雄收購海山煤礦的房產資訊,敘事—論述—資訊—圖像—影像的共謀還遠遠不夠,高俊宏於雙年展期間舉辦重返拍攝地放映的活動,帶領著一小群觀眾甚至不惜以非法進入的方式,重新回到這些失能空間觀看《博愛》。加入行動這個關鍵要素後,觀眾成為一種臨時社群,促使《博愛》從影像上的感知擴延為身體的感知,以往從藝術家組織出發的意識形態與體制批判,在此轉向揭露新自由主義的暗流,凡放映行動參與者皆共同承接集體創傷的共感,高俊宏所創造的「歷史敘事」取代觀眾生命史「實際經驗」,透過影像與放映行動讓事件與事件從視覺藝術的範疇成為立體的身體感知經驗。
那,更進一步的行動之下,在大豹社相關研究創作之後,高俊宏成為一位人類學家或歷史學家了嗎?這不僅是近年藝術領域觸及歷史考察或田野調查時常常會遇到的質疑,另一方面古典「行動效力」的質問也依舊尖銳地存在。在此我們先繞道海登.懷特(Hayden White)提到麥克爾.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認為有兩種歷史,一種是「實際的過去」,意思是記憶、訊息和知識的組合,關於自身與社會集體過去的認知,我們得以參照藉以解決日常問題的知識性歷史;另一種則是「歷史的過去」,即是史學家建構過去時態的圖景,奧克肖認為後者是「沒有人經過的歷史」,只存在研究者的頭腦與論述中,只是大量的「陳述」,對於現實毫無實際用處;(註6)而海登.懷特試圖打破兩者之間游離的區別,以跨學科的敘事修辭學,讓意識形態進入歷史事件與事件產生關聯,並不畏懼詮釋成為動搖歷史真實度的對手,強調敘事之於歷史的重要性。而再回到高俊宏近年走入山野踏查的種種實踐,他同樣以大量的史料調查、地理考察、田野訪談創作了大豹社相關系列展覽,以及出版了《橫斷記:臺灣山林戰爭、帝國與影像》和《拉流斗霸:尋找大豹社事件隘勇線與餘族》兩本著作,同樣他在《拉流斗霸》作者序如同《小說》般再次強調了體裁與創作視角,他說「書寫」擁有更多描述空間,因此即便援引龐大的文獻資料,這本書仍然並非是文史調查或研究報告,(註7)就藝術家本人來說「希望在影像的國家敘事與個人敘事之間,形成辯證。」(註8)某種非虛構的敘事、寫實但非全然現實的書寫,逐漸讓不可知、且無人在乎的帝國暴力在這之中顯影出來並獲得重視,「大豹社事件無疑是二十世紀初的世界史,或至少是對抗東亞帝國與資本主義史的一部分。」(註9)
與之前90年代以身體作為自我辯證的介面、廢墟計畫中的繪畫乃至《博愛》,高俊宏作為藝術家逐漸降低自身在作品中「給予意義」的角色,他身體力行的實踐反而讓位出一處空白之地,以大量的田野資料與思考辯證組織這片空白,讓一般視為「取材對象」或「敘事背景」的被觀看客體成為作品中真正賦予意義的敘述者,藝術家的身體與論述為其穿針引線並留下紀錄,非純粹史學或人類學的辯證過程,讓藝術得以透過行動與跨學科介面重新提供一種認知/認識,而回到人文領域的展覽與書寫,則讓認知重新轉化為感知,為像是大豹社事件開拓出知識建構層面的歷史,抑是可以感知的生命政治狀態。

空白與讓位之間 走進真實殘響的陳界仁
高俊宏在《拉流斗霸》後記〈如果有「田野」,我很難告訴你我所經歷的〉述說原先走進山野是為了自我重建,但許多奇妙的因緣際會讓他走上探索隘勇線的旅程,其中他耗費大量心力時間被視為「田野」的實踐,對他自身來說卻是「我對『田野』二字的定義並不指向人文科學的畛域,而是關於社群(或族群)的運動。」(註10)從《諸眾》到大豹社相關研究,高俊宏逐漸具有某種行動是為了連結社群的意識,或許並非特意為之,而是自然而然行動必然產生或多或少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性,但又並非關係美學透過白立方或美術館空間內,以作品為催化劑觸發社群形成的作法,而是傾向因行動而自然建立的社群關係。
而在陳界仁以往作品中亦多次出現並強調的「臨時社群」,像是《加工廠》聯福製衣廠的成衣女工,《殘響世界》樂生病患、《幸福大廈I》中的工作與演員團隊來自各個邊緣團體……幾乎每一件作品都會建立一組臨時社群。但也讓藝術家面臨創作倫理上的批判,像是當臨時社群成為藝術家個人作品被強勢展覽機制所收納之際產生的權力質變,(註11)或是強大的情感渲染力使作品中的邊緣團體成為詩性的審美。究竟藝術家該與創作中產生的社群該維持怎樣的權力關係,才符合藝術的或甚至社會的、政治的倫理?


在此我們先擱置這個問題回到《再現空白》,展演現場彷彿以弔唁的形式將可悲慟的生命主體直接觸及藝術家數月前過世的母親,黑白原點交替的低限影像與雖名為表演,但身體空置於劇場中央,僅留舞台側一格小方窗,觀眾僅能看見陳界仁的手,拿著講稿緩緩並聲音低沉地述說以往僅能在訪談中側面瞭解到的家族史;隨著表演結束前藝術家一張一張焚燒約莫二三十張講稿的氣味,接著陳界仁默默退場,確實以影像而言僅僅再現了某種空白。被抽離的極簡影像不復見以往陳界仁謂之「諸眾」的邊緣團體,必須仔細聆聽才不會漏掉的自述中,約莫90分鐘的表演期間至少重複十幾次「我們都是造幻師所造的幻像之人,但幻像之人,也可以成為能製造幻象的造幻師。」在此陳界仁作為造幻師所創造的空白或許就是作者反省作者所佔用的位置,而此一位置,在《再現空白》中賦予了「讓位」的意義。亡母、癱瘓並已過世的大弟、在遊戲機中藏著LSD迷幻藥的大哥……成為敘事中的「意義賦予者」,他們的生命經驗共同協作了《再現空白》中傳達的共鳴感。
而這種共鳴感,首先取消以往影像作品中「臨時社群」的形象與集體敘事,即便是家人,母親的生命史、弟弟的生命史與陳界仁自身的生命史合而不同,因此這種共鳴並非是群體一齊發聲;是點到點的從母親到弟弟、到大哥到個人,最後透過劇場的形式讓觀眾直接感知陳界仁的「不在」再現了作者的空白,這個空白恰好就是必須讓位給臨時社群的召喚,雖然是他但又不只是他,連同以往作品中的女工、樂生病患、臨時工人、社運者彷彿一同在此現身;不再以一種寫實主義的底層關懷運鏡去拍攝可悲慟的苦難主體,不再強調多大程度的「反映現實」,承認身為「造幻師」作者的位置反而製造出空白,生命政治的「意義」而非「現象」在此顯影。

因此回到,當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產生的社群,我們應該思考的是生命政治本身的辯證,如同高俊宏曾說藝術的效力應考慮的是「社會性」而非「社會運動性」(註12),而放置在當代藝術依舊不斷述說國家權力、威權治理規訓的議題下,對於像是「取材對象」或「臨時社群」各自歧異的私人生命史,藝術作品難道應該繼續「代言」、「代理」或甚至「監視」,他人生命?高俊宏在《諸眾》指出即便只有兩個人社群比佔領更為重要,意味著行動介面所產生限定式、無存檔式的社群參與是有相當侷限性的影響效力,尤其當我們把藝術行動放置在社會運動的語境之下去審視時。而或許藝術家也難以否認,「藝術-行動」之後所產生特定社群的感知,必須透過展覽、書寫、論述的表述賦予觀眾某些認知,而觀眾能多大程度的將這種認知轉化為感知則不可知,但我們必須認知到多大程度的寫實,也非現實;而多大程度的虛構,亦有其寫實內涵。藝術並非特定群體生命的複寫紙,關於藝術自身、生命政治、意識形態辯證並甚至是重新提問的能力,必須兼容並蓄、更細微地去考量。

想像的庇護所 做與不做之間的中空之地
暫時改寫陳芯宜跟拍海筆子十二年的紀錄片片名「大帳篷—想像力的避難所」,並取用片中團員對於帳篷的理解:「什麼叫做『創造了一個場域』出來,如果在一個地方,某一個人開始生火,升起一團篝火那個事情,對我來講是帳篷的場域。包括點火的人,照顧火的人,包括說被火吸引過來的人,有的時候添柴火的人,所以很多不同的狀態在那個火的周圍。」就高俊宏和陳界仁以影像或行動創作的場域,高俊宏在大豹社相關創作書寫計畫中並非是社群或場域中那個生火的人,大豹社事件以及其族人原本的生命史就已然存在,或許藝術家更像是照顧火的人或是添柴火的人,讓更多人被火吸引成為一種因社群而觸發的場域。而陳界仁在影像創作過程中,在鏡頭前後方皆由他所組織運鏡形成的臨時社群形象,在《再現空白》某種程度上他放開作者論的視角,將空白讓位給沒有影像的想像力(就筆者觀察,演出當晚許多人面對低限重複的影像後來皆是選擇閉眼聆聽)。想像力從來不是一種抽象的能力,它是開啟我們如何從「認知」轉換到「感知」的能力,即便藝術創作中社群領域的形成對觀眾有理解之侷限,但依舊是開啟臨時社群與觀眾社群的一扇暗門,願者入門。而走過大聲疾呼反抗體制的年代與創作歷程,選擇「不做什麼」比「做什麼」對高俊宏與陳界仁而言,似乎成為更重要的思索。
延伸閱讀|【專題】可是,我們回不去了,之後:藝術家的自我復刻

註1 童詠瑋,〈現場藝術的時態:專訪C-LAB年度展覽「Re:Play 操/演現場」策展人莊偉慈、王柏偉、林人中〉,《典藏ARTouch》,2020年10月27日。(檢索日期:2021年2月18日)。
註2 高俊宏,〈一創作就矛盾:晚近二十年台灣藝術身體徵候〉,《陀螺》,台北:遠足文化,2015,頁125。
註3 參見在地實驗計劃論壇「二十年的謎題」系列第三場:「樹不知道捷運通往哪裡:有關一種滯後的創作觀」(高俊宏),2015年9月21日。(檢索日期:2021年2月18日)
註4 高俊宏,〈破鏡之緣:東亞藝術社群〉,《諸眾》,台北:遠足文化,2015,頁281。
註5 高俊宏,〈前言:一瓶烈酒〉,《小說》,台北:遠足文化,2015,頁23。
註6 海登.懷特,〈對歷史負疚嗎?保羅.利科的長時段〉,《敘事的虛構性:有關歷史、文學和理論的論文(1957-2007)》,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頁413。
註7 高俊宏,〈作者序〉,《拉流斗霸:尋找大豹社事件隘勇線與餘族》,台北:遠足文化,2020,頁31。
註8 高俊宏,〈自序〉,《橫斷記:臺灣山林戰爭、帝國與影像》,台北:遠足文化,2017,頁17。
註9 同註7,頁27。
註10 高俊宏,〈如果有「田野」,我很難告訴你我所經歷的〉,《拉流斗霸:尋找大豹社事件隘勇線與餘族》,台北:遠足文化,2020,頁387-391。
註11 吳祥賓,〈斷裂的評論:論陳界仁「體制內反體制」的內在矛盾〉,《典藏ARTouch》,2018年11月06日。(檢索日期:2021年2月18日)
註12 高俊宏,〈2021-後寮現地創作計畫〉,《ARTalks台新藝術網》,2021年1月30日。(檢索日期:2021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