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追憶
在討論蘇匯宇此次最新個展「午夜場」之前,我們得先思考一個基本問題:長久以來,藝術家透過藝術創作對電視的媒介特性,以及其所鏈結之影視文化的種種執戀,只是一種單純的懷舊式凝視嗎?因為藝術家確實曾在他的創作自述中提到「『電視兒童』世代即將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網路兒童』,回想我2004到2007年的這些作品,其實就是一種個人見證,見證『電視兒童』的年代,見證一種思維習慣的特質、難題與即將被淘汰的殘酷事實。」(註1)因此他的創作,只是代替同樣歷經數位化與網路革新浪潮的我們,捕捉屬於舊時代影音感性的最後一抹身影嗎?抑或,僅僅是因為影音媒介環境的日新月異,因此藉著藝術家的眼睛回望,電視機世代所屬的那種相對被動且片面接收的觀看形式,如今顯得陌生而新奇罷了?
不!顯然不只是如此。我認為若是太過側重「懷舊」的概念,反倒會讓蘇匯宇作品的閱讀面向變得扁平。因為,雖然藝術家2010年以前的作品確如其自述所言,有見證一個年代逝去的意味,然而在《電視、藥物與家庭錄影帶:使蒂諾斯家庭實境秀》(2010)之後,他已發展出一種疏離、迷濛、冷冽的影像語彙,用以刻畫人游離在日常脈絡內外的精神狀態,以及各種失魂般的恍惚身體。此一冷冽影像語彙的確立,為他晚近幾年創作問題意識的擴延─從大眾文化的陳套(cliché)的致敬式重演、對媒介景觀裡的特異感性之粹取,到身體情慾或流竄或壓制的反覆審視─提供了極其穩固的基礎。而「午夜場」正是奠定在此基礎之上的最新推進。透過對高速攝影機、HD高解析畫質等數位播放機具條件的熟練運用,蘇匯宇構築出一個具有高度反思性的影像世界,其創作姿態早已不是單純地朝向過去、背對未來。與其說他的影像美學是對逝去年代影視文化的懷舊凝視,不如說是以此做為觸媒,召喚那些看似已隨時間封存的身體感性及欲望結構;與其說他打開的是一個回望歷史的窺視孔,不如說是以此做為思考契機,邀請觀眾共同聚焦台灣自戒嚴時期以來,種種纏繞在影視文化周邊的集體記憶與現代性經驗。

蘇匯宇│自瀆有礙身心之說不可信(金賽博士) 錄像、繪畫、攝影與空間裝置 160x100x138cm 2015 攝影/李旭彬 絕對空間提供
羞愧的觀看
藉由與策展人游崴的緊密合作,「午夜場」企圖呈現更為宏觀的文化剖面。以台灣1980年代被官方文化審查機制極力排除、管束的情色書刊、流行音樂,以及綜藝文化為線索,直指戒嚴時代黨國機器亟欲構築的健康寫實文化觀之陰暗面,並且引領觀眾反思儒家思想體系底下,種種教條化的社會禁制。不過,策展人與藝術家並未採取簡化的社會批判姿態,而是充分利用前述冷冽的影像語彙,來捕捉那些總是被主流社會貶低為齷齪、骯髒、背德的情慾關係。在呈顯各種性愛身體或者想像幻境時,蘇匯宇以強大的影像掌控力,給予我們一種毫無激情,甚至異常漠然(indifferent)的凝視,彷彿如果不進行如此疏離化且肅清任何氾濫情感的「感性調控」,那些不斷溢出既有社會框架之外的欲望身體,就不可能在影像之中凝結成形。換句話說,適度壓抑影像在感官上的誘惑力,為的是逼現出更為幽微的情動力(affect),而不是某種純粹美感塑造的考量。其次,疏離化的操作也是為了讓觀眾得以關注到影像內容之外的其他空間布置層次,譬如裝置現場對於觀看機制的特殊設計。

蘇匯宇│自瀆有礙身心之說不可信(金賽博士)(影像擷取) 錄像、繪畫、攝影與空間裝置 160x100x138cm 2015 双方藝廊提供
《自瀆有礙身心之說不可信(金賽博士)》即是典型的例證。這件作品在其木作結構旁側設有一個圓形窺孔,一次僅能允許一名觀眾往內探看木箱內播放的影片。儘管影片本身具備相當的挑逗性,以詭譎幽暗的診間、手術台、皮帶銬練,以及赤裸白晰的女體等元素誘引觀眾的目光,然而圓形窺孔被刻意降低的高度,很快就會令任何一位好奇靠近這件作品的人意識到,她/他唯有保持在幾近偷窺行徑般的尷尬姿態,才有可能看完整部影片。這種充滿羞愧的窺視機制無疑是藝術家的巧思。且不同於數個月前在台南絕對空間展出時較為隱蔽的空間樣態,「午夜場」選擇空曠寬敞的展聽放置這件作品,其圓形窺孔更是直對著展間入口。初步來看,這確實有可能削弱觀眾趨前窺探的意願,使之淪為一個只被遠觀的尋常雕塑物件。但我認為,毫無任何一點遮蔽的空盪展廳,使得窺視行徑勢必得在眾目睽睽的情境下進行,這反倒強化了作品所蘊含的「羞愧的觀看」之張力。(註2)再者,雖然裝置與展呈空間的「外部」關係,確實可能促進或減損這件作品的窺視機制,但該機制主要還是內建在作品的「內部」;不想將之誤讀為純粹雕塑物的任何一位觀眾,仍必須涉入藝術家特意設置的這種介乎看與被看的權力關係,才可能對該錄像裝置進行全面性的細緻閱讀。要言之,蘇匯宇對愛慾的刻畫與思考,顯然並沒有侷限在做為美感客體的影像一端,而是充分利用展呈機制與作品形式的巧妙設計,直接體現在觀眾的身體感知脈絡中。

蘇匯宇│臨風高歌 雙頻道錄像裝置與攝影 投影尺寸依場地而定(攝影尺寸150x110cm;相紙材質:Canson Platine Fibre Rag 310gsm) 2015 双方藝廊提供
凝結的身影
敏感的觀眾也許會對藝術家這種疏離化的影像操作,感到一些不安:為了使不可名狀的欲望凝結成形,成為可觸可感的批評對象,藝術作品似乎無可避免地也必須對欲望進行種種的調控與管制。此種時時阻斷欲望流動的作法,難道不會成為自身批判控訴的對象嗎?對此我採取較為樂觀的立場看待。這是因為,一來如先前所述,藝術家的感性調控並不是為了某個抽離脈絡的美感塑造,當然,也不是出於道德諭令的整肅清理而來。其二,唯有對欲望本源反覆進行重探與重構,藝術家才可能跳出情色文本原初的感官愉悅表達陳套,繼而更深刻地在影像裝置之中,逼顯出該文本最特異的感覺存有。而後面這點,正是佔據雙方藝廊展廳主要位置,且在聲響效果上為整檔展覽定調的《臨風高歌》所試圖凸顯的。
初步觀之,《臨風高歌》只是對已故藝人高凌風所主持的同名節目的致敬之作;只是藝術家對豪華燈光舞台、清冷乾冰、合音天使,以及迪斯可舞球所交織之時代氛圍的無限追憶。然而正如游崴的描述:「乾冰與燈光牆切斷了現實,創造出某種短暫的、只在景框中有效的情色效果,以至於在乾冰中冉冉現身的物事都變得如此性感。」(註3)《臨風高歌》其實是一個漢密爾頓(Richard Hamilton)式的提問:究竟是什麼使得被乾冰烘托起來的一切如此性感,如此地與眾不同?是因為高凌風當時引介、改編的迪斯可舞曲表演風格,不斷踩到戒嚴時期文化審查界線,因而顯得既危險又充滿誘惑力?還是因為這不過是開到荼靡花事了,曾經盛極一時的星途如今也只剩下荒蕪空盪的舞池,供人憑弔早已離席的藝人身影?對此,蘇匯宇並未給予任何清楚的答案,他只是充分利用數位播放機具最基本的迴圈機制,把觀眾徹底擄獲在當年暢銷金曲〈惱人的秋風〉永恆回歸的樂音裡;隨著伴奏樂隊一次又一次地反覆演奏,即使不曾經歷這段歷史的觀眾,也能輕易感受到那不斷被聲響推擠、堆疊的頹廢感性。再往內走至屏幕背面,我們則會看到藝術家藉由三道閃爍的舞台燈光,將孤獨的主唱身影凝結在一個宛如祭壇畫般的影像空間裡。在此,縱使高凌風的身體從來沒有真正出現過,藉由樂音與影像皆有所殘缺、相互裂解的布置方式,《臨風高歌》成功給予我們一種極其清晰、鮮明,同時又蒼涼無比的感覺存有。

蘇匯宇│超級禁忌 雙頻道錄像 依場地而定 2015 双方藝廊提供
男學生背後的手
不過,「午夜場」真正的高潮是另外一件雙頻道錄像裝置《超級禁忌》。一方面,自然是因為金士傑精湛的演技,使看過的人都忘不了這位偷閒的中年上班族,在某處四下無人的公園密境裡,樂不可支地朗讀色情小說內容的猥褻場景。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影像並未含蓄地停留在露骨文字的想像層次,而是隨著那句性幻想最終獲得滿足的「真是個風和日麗的一天!」整部影片如背景裡奔騰不止的瀑布溪流一般,瞬間延展成一幅由許多性愛畫面鋪排而成的春宮畫長卷,從使用輔助按摩器的女女歡愛、三人交媾、恣意流淌的體液,到高難度體位的大膽嘗試,《超級禁忌》向觀眾徐徐展示一組時間凍結的宏大性愛雕塑群像。不過,這些百無禁忌的畫面並不只是中年上班族性幻想的具體延伸而已;它們同時也是一種挑釁影像,使藝術家得以直探潛藏在整個影視欲望結構背後,更深層的禁制暴力問題。
其中最關鍵的轉折便是影片中段,一位沉浸在情色書刊裡的身體圖像,表情既興奮又充滿焦慮的男中學生,手中刊物旋即被後方數名查緝人員奪去的扣押橋段。高速攝影極其緩慢的速度,讓這段僅佔據整部影片一小部分的拉扯畫面,成為《超級禁忌》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暴力場景。男中學生的形象,除了指向藝術家性知識啟蒙經驗之外,其著迷、耽溺、害怕與驚恐兼而有之的複雜心理狀態,也帶出整個戒嚴時代看似健康正面,實則無比窒悶的情慾壓制精神結構。因此,相較於影片後半段那些既聳動又豔麗的性愛圖景,躲藏在男中學生身後,一隻隻不知何時會襲來的查緝之手,恐怕才是《超級禁忌》的真正主題。因為,從服裝儀容、髮禁、門禁等日常生活層次的基本管控,到孝道倫理、國家認同乃至於性傾向等思想層次的重重箝制,這隻不斷體現著戒嚴體制與儒家思想教條最為陳腐、八股一面的禁制之手,從戒嚴時代以來就不曾真正剔除過。甚至,它總是以秩序、品德、貞潔等荒唐的面目復返,阻礙社會更為多元且開放的情慾觀/身體觀之交流、展示。如前些日子,文化部電影分級審議委員以違反刑法第235條妨害風化罪的理由,透過拒絕分級審議之方式變相封殺國際影展上廣受好評的電影《性本愛》(Love ,Gaspar Noé),足以顯見保守的道德禁制力量從未離我們遠去。由此觀之,《超級禁忌》所欲對抗的遠遠不是過往時代的思想/身體規訓,而是徹徹底底的現在進行式。

蘇匯宇│超級禁忌 雙頻道錄像 依場地而定 2015 双方藝廊提供
從恍惚到清醒:兩種身體
整體而言,「午夜場」已在蘇匯宇創作發展脈絡之中,佔據一個極其關鍵的轉折位置。這不僅僅是因為他精彩地推昇自己的問題意識層次,使其影像語彙大幅度擴張他過去反覆刻畫的,出神的、疏離、恍惚的身體;「午夜場」清楚地向我們展示,這具慾望身體如今已能承載更豐沛而厚實的文化意涵。但尚有另外一具並未呈顯在作品影像之中的不可見身體,也被蘇匯宇一併推進了。意即做為其創作發想之起點,午夜獨自一人轉著電視,徹底沉浸在影像中的那具耗費身體。藝術家顯然有意擺脫傳統上對後者的各種貶抑;在過去,它總是被批評只是單方面接受歐美日影視文化的宰制邏輯與思想殖民,根本難有任何一點主體性。但如今,至少就「午夜場」所展示的問題意識強度來看,答案顯然不全然是否定的。因為,總以「電視兒童」自居的蘇匯宇,不正是透過藝術創作一次又一次地證明,即使是對這種被動的耗費身體(暨其觀視慣習)的深切執戀,依然有可能翻轉出對自身歷史、文化語境的深刻洞見?而這種從迷濛恍惚到清晰警醒的精神樣態跨越,以及勇於接受自身文化的種種歪斜與不堪,不也正是其創作語彙中最為珍貴,同時也最能給予我們啟示的地方?
Tag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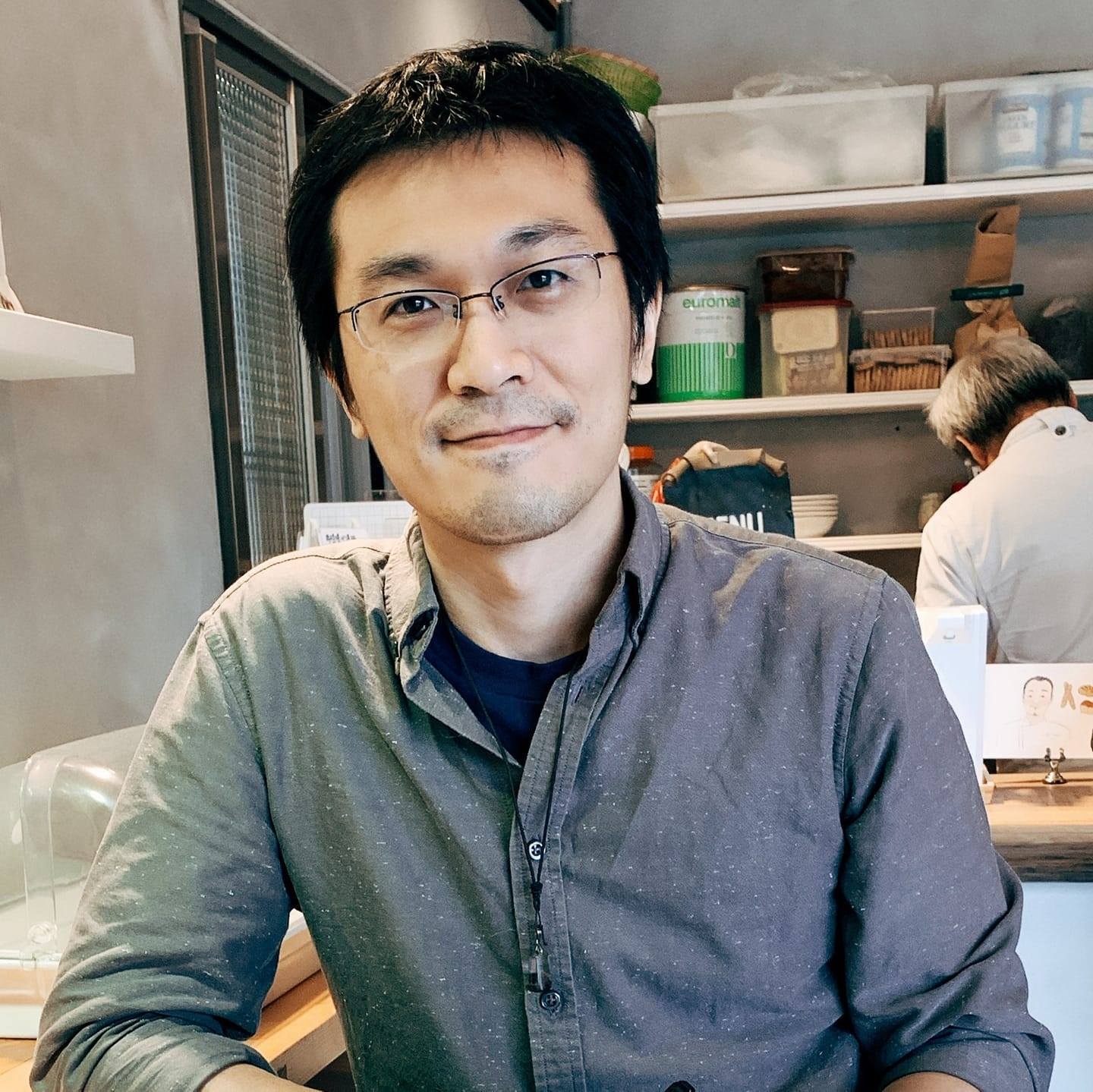 王聖閎( 13篇 )追蹤作者
王聖閎( 13篇 )追蹤作者藝評人,現為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任台新藝術獎提名觀察人(2017, 2018, 2021)。主要研究興趣包括當代錄像、行為表演及身體性創作;關注當代加速度政治下的生命政治課題,聚焦於科層機器對身體行動和耗費模式之影響,並且在此基礎之上,持續反思在地藝術理論的生產與擴延。文章散見於《典藏今藝術》、《藝術家》、《現代美術》,以及台新藝術獎「ARTalks」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