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史視野的斷裂與缺席
龔卓軍近期在一篇回顧當代藝術十年發展的文章裡,對當前的「田野」模式提出建言。他指出,台灣在地庶民文化雖然蓬勃發展,如數量眾多的廟宇建築雕刻、傳統戲曲音律,以及圍繞著宗教信仰而發展出的各式身體展演,都有極具生命力的表現和積累。但這些民間藝術(暨其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卻幾乎與當代藝術平行無涉,甚至被後者徹底「外部化」、「他者化」,視為無物;只有那些能與歐美藝術話語系統對接,或者曾經被殖民者之美學標準所涵蓋的創作區塊,才會得到藝術學院教育與美術館展演的青睞,形成一種「自我分裂的藝術史觀。」(註3)
這種民間藝術與民俗技藝被異教化,甚至淪為自我賤斥、自我降格的存在,自然與台灣過往蒙受黨國體制殖民教育所強加之品味階序,以及學院教育偏重媒介特定性探索的形式主義美學觀,脫不了干係;以致於,許多創作者從事田野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必須面對如何(憑一己之力)恢復並重構自身歷史/檔案的問題。因此,龔卓軍所提之庶民文化與當代藝術的二分斷裂問題,確實可從藝術史的角度加以拓展、推進。換言之,民間藝術這塊「田野」沃土的棄置,必須與當代藝術和傳統藝術史研究看似極其親近,實則幾乎不相往來的長久弊病放在一起思考。證諸現今藝術學院的知識體系設計與養成思維,藝術史的方法論、問題意識及核心關懷,都處在一個「看似必要,實則邊緣」的地位;相較其他影響當代藝術發展甚深的領域,如哲/美學、社會學、精神分析,乃至人類學知識概念所帶來的啟發性,藝術史顯然存在諸多從理論到實踐層次的扞格,始終未被深思。當然,這也是因為傳統藝術史研究與當代藝術之間存在諸多意識型態上的分歧,因此在學院現場,我們時常可見藝術史研究生與美術系所學生毫無交集的怪異情景。做為一個略顯老態的學科,藝術史研究固然有其保守封閉的問題有待解決,但視覺藝術領域對於它究竟需要怎樣的藝術史知識奧援,也欠缺深刻的反思。除了少數藝術史相關系所的特意維繫與經營(但如今在少子化衝擊之下,亦是風雨飄搖),絕大多數時候,藝術學院裡的年輕創作者都是被直接拋入以歐美當代藝術跨國機制,及其美學概念體系所形塑的「當代」氛圍中。

無垢舞蹈劇場創立者林麗珍。(牽猴子整合行銷提供,金成財攝影)
缺少現當代藝術史縱向與橫向的連結視野,特別是針對從日治時期至解嚴前後,一種以主體性和解殖意識為基調的反覆書寫與重構行動,那麼當代田野實踐依舊會欠缺一塊必要的知識框架,來整合它與民間藝術暨庶民文化之間的關係。必須再次強調,這裡指的並不是當代藝術工作者欠缺藝術史的涉獵和視野,而是對許多人來說,藝術史的知識建構經常是處在一種「僅憑個人努力」的自我惡補情境。正因為這種藝術史教育的斷裂和不均勻,因此縱使過去有前輩畫家如李梅樹對三峽清水祖師廟重建工程的深入參與,有席德進對傳統民居與民俗器物的蒐羅研究,甚至在1990年代初的繪畫裡(如楊茂林、黃進河、黃明昌等人)都還有一種在視覺語彙上將鄉土意識延續至台灣主體性追尋的在地考掘企圖,這些前人的成果都未被有效承繼。事實上,這些在「民族誌轉向」之前的田野探索並不是消失了,而是它們多半只被視為個案,繼而被傳統名人傳記式的陳腐藝術史書寫模式,編碼進其個人生平軼事(如強調此類生命經驗如何成為藝術家個人的「創作養分」),而不是被轉化成一種可供後人援引參照的田野方法論。由於前輩藝術家們關照在地文史細節的特殊技術,其匯整不同感覺結構與圖像系統的「感性知識」,並未凝聚成有系統的「田野」模式,因此年輕創作者們自然每一次都必須另起爐灶,土法煉鋼地「自力治史」。簡言之,缺少藝術史的關鍵橋接與轉化,意味著我們喪失的是一整部從當代視角回觀的田野筆記。

陳冠彰│地方腔-尪姨說:「」 「臨時公廨」:豬頭骨、將軍柱(竹子)、祀壺、香蕉葉、圓仔花、檳榔、罐裝米酒、以上借自社子公廨 2014 藝術家提供
反身性思考之承繼與藝術田野的特質
或許有人會疑惑,就算當代藝術與傳統藝術史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但難道其他文學、戲劇、音樂、舞蹈等領域的田野知識,沒有在當代的跨域展演實踐裡,起到潛移默化、橫向流轉之功效嗎?譬如文學在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有文化思想上的全面性震盪,紀實攝影也有捕捉在地生活細節的觀看傳統,而舞蹈/戲劇史長久以來,更是保有對民間信仰儀典的持續性轉化(如林麗珍與其無垢舞蹈劇場的身體訓練和美學思想)。這些相近領域的實踐典範,應該能夠「滲入」視覺藝術領域的討論才是。
答案自然是有的。但這種橫向跨越的問題意識交流(庶民文化的轉化參照),卻也是到非常晚近的這幾年,特別是在表演藝術與視覺藝術開始共享穩固的展演與評論交流平台之後──如台新獎的改制與藝術雜誌的跨域欄位設計──才得以真正實現的。而這也凸顯台灣「田野」模式當前最重要的課題,其實依然是如何承繼其他領域之知識與反省成果的問題。姑且先不論藝術相關科系,視覺藝術界在沿用人類學知識與方法時,其實很少將後者對自身學科規範及倫理的反省一併帶入。這並不是說,當代藝術非得遵守人類學的「行規」,而是藝術工作者對於自身田野實踐的特殊性與限制,仍缺乏充分的討論。

陳依純│林水源傳奇第一集 2013 藝術家提供
舉例來說,人類學家經常必須仰賴長期而深入的田野實踐,來建立她/他對某一文化從政治、經濟、宗教到親屬等分支層面,兼顧特殊細節與整體全貌(holistic)的詮釋觀點。人類學家有其從一個完全的局外人,逐步成為局內人的特殊生命歷程。這一方面具體根植在她/他與報導人之間的關係演變,另一方面也體現在人類學家往返於田野地與學術場域之間,一系列從空間到心理距離的轉換經驗。再加上民族誌書寫總是涉及複雜的再現權、互為主體式的「多聲」(polyvocality)表達,乃至與報導人之間難以平衡的知識落差問題,因此人類學家的自省總是格外引人入勝,極具參考價值。藝術家的田野同樣具備如此關鍵的生命歷程,但相較之下,現階段只有部分創作者意識到,充分展示上述這種反身性思考,有時比作品本身的完成更重要。因為比起只能依靠文字概念工作的人類學家,藝術家更有條件提出一種介於理性知識與感性形式之間的交織纏繞實踐(entangling practices),來揭示理解某一文化的特殊視角,並且向觀眾充分闡釋她/他究竟穿梭在哪些相異的感覺結構之間,同時又開啟了何等新穎的文化溝通介面。

張徐展│紙人展-房間 靈靈壹 現場裝置 2015 藝術家提供
而這也順勢回答了文章開頭所提及的「藝術家的觀察者位置與話語權力究竟為何」的問題。簡言之,相較於正統的人類學路徑,藝術家的田野實踐更有機會去揭露一種如幽靈一般,徘徊在不同文化疆域與符號系統之間的特殊轉譯者/協調者位置,從而啟動另類的文化生產。譬如藝術家陳冠彰針對西拉雅族年輕尪姨展開長期訪談和故事採集的田野實踐,便是相當好的例子。因為他不僅會在言談間,清楚反思他做為藝術家、文化研究者、聯絡者的游離位置(註4),更讓當代藝術與祖靈及神祇的世界產生奇異的纏繞,甚至催生西拉雅語研究翻譯的回饋性生產。這些成果是任何知識領域都無法輕易歸類的殊異混種物。
要言之,把我們帶往難以界分的未定疆域,無疑是當代田野實踐最可貴的特質之一。這讓我想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在談論何謂人類學時曾說過的一段話:「人類學(或者該說社會人類學或文化人類學),事實上更接近一個人年復一年的設法搞懂它到底是什麼,又該如何去實踐它,而不是透過『使人服從的系統性方法』或正式的『經由命令與控制的訓練』來逐步灌輸的玩意兒。」(註5)仔細想想,若把紀爾茲這段話裡的「人類學」替換成「藝術」,顯然也言之成理。藝術的魅力,何嘗不是因為它總是擁有一種藉由自我否定與顛覆,來獲得向前推進的批判性力道?少了這種追尋,少了大膽肯定它只能不斷走向他者、積極踏入未知的勇氣,藝術將不再是藝術,而是如紀爾茲所言,只是一個灌輸規訓方法和美學權威的空洞玩意兒。
從人類學家的職業生涯開始,田野研究便是懷疑的母親與褓母。而懷疑正是卓越的哲學態度。這種「人類學的質疑」不只包括知道人是一無所知的,更包括堅決地揭露人因其無知而認定他/她所知的,以打擊或否定人們隨出生而來所培養的觀念與習慣,並代之以最能反駁它們的觀念與習慣。(註1)
──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人類學的視野〉(The Scope of Anthropology)
「田野」的危機
台灣當代藝術正經歷一次值得關注和梳理的「民族誌轉向」,不僅「田野調查」已成思考藝術實踐模式的重要關鍵字,我們也看到愈來愈多藝術家提出的創作命題、表現形式及工作方法,可從「當代藝術與人類學之合作關係」的角度重新加以審視/詮釋。許多評論者皆已針對這個現象提出各自的觀察評述,我自己則是從2013年的一篇文章開始參與這項議題的思考和討論。(註2)
這篇文章的寫作目的,並不是為了增補更多符合此一轉向的作品案例,而是隨著「田野」一詞逐漸受到熱議,也開始出現許多不同面向的省思,包括概念稀釋的問題、成為妝點創作之修辭的問題,以及更重要的方法論與實踐倫理究竟如何評估檢驗的問題。簡言之,一方面,我們確實看到嶄新的命題與方法,正隨著誠懇認真的藝術家們的投入而快速發展著。但另一方面,也的確存在一些素樸而初階的踏查採集被冠以「田野」之名,以致於,藝術家被質疑其田調資料完全沒有經過任何嚴謹的學術檢驗標準,也未必與其田野社群展開實質對話,恐有淪為業餘民族誌的危險。我們究竟該如何思考這樣的指控呢?當藝術家開始像人類學家一般工作,其實踐成果究竟與後者有何異同?而當「田野」歷經藝術上的挪用轉化,藝術家的觀察者位置與話語權力又該如何理解?這些都是有待我們反思與回答的問題。
其次,人類學方法中最重要的精神之一,是透過不同文化之間所形成的比較觀點,來重新省思研究者自身文化裡既定的價值觀、意識型態與文化偏見。因此人類學遠比其他社會人文學科,都要更加注重反身性(reflexivity)在知識建構中的重要地位。不少深刻的人類學著作,其起手勢經常就是基進的自我批判和質疑,而許多當代最尖銳的文化批判聲音,也往往出自人類學界。不難理解,這種批判精神上的靠近,顯然正是當代藝術與人類學會走在一起的原因。但我們仍必須仔細檢視,民族誌轉向中的台灣當代藝術,究竟挑起哪些反省自身機制常規與美學偏見的批評意見?因為僅止於差異文化的納入,並不會保證機制的顛覆與翻轉(它亦可能是一種假性的開放與收編);我們仍須追問,這些反省究竟有無形成大範圍的議論,使當代田野實踐不會掉入將異質文化的符碼再現,挪作一種類型化標籤的危險?

陳冠彰│地方腔-尪姨說:「」 田野故事多語文稿 2014 藝術家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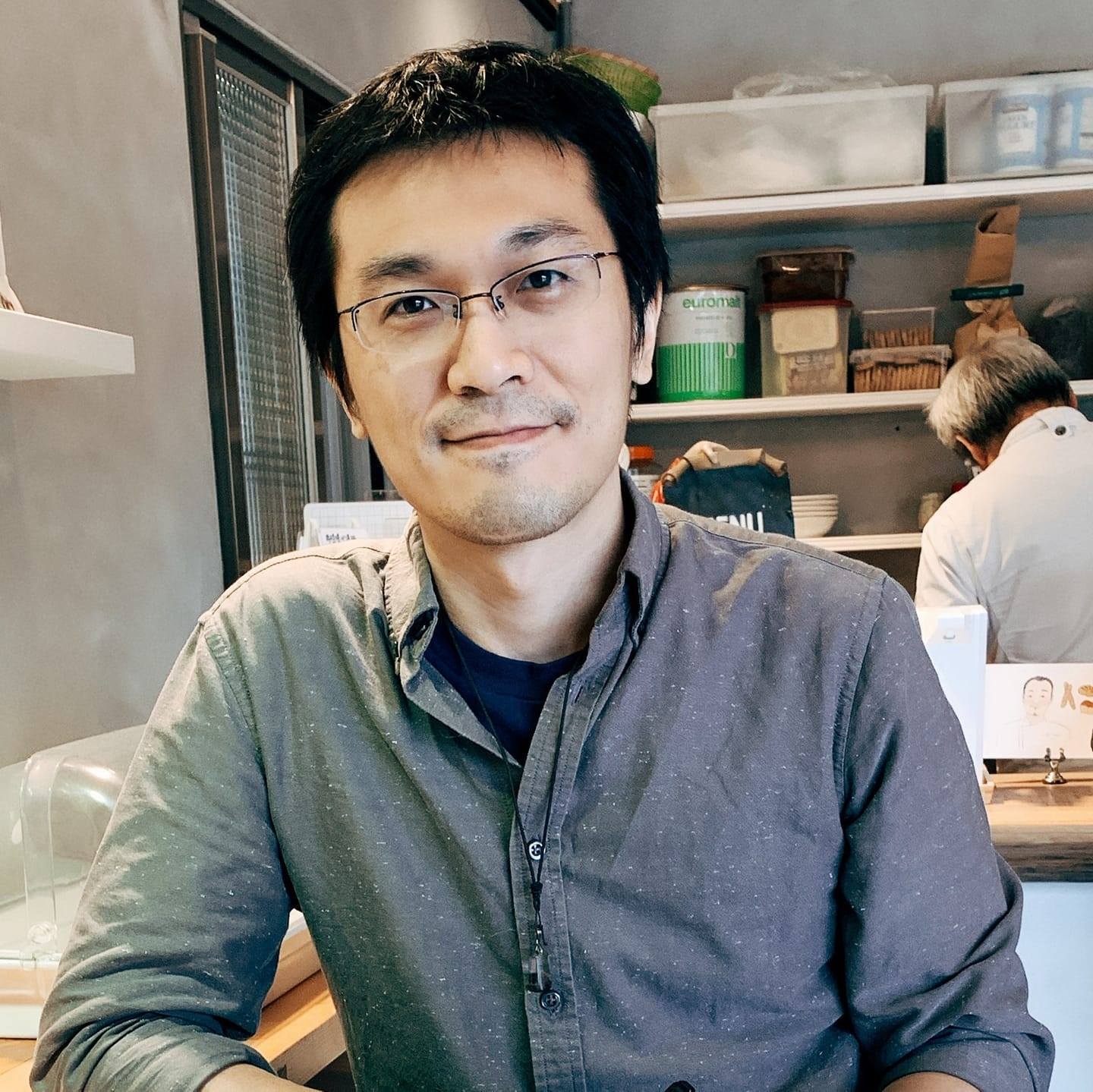 王聖閎( 13篇 )追蹤作者
王聖閎( 13篇 )追蹤作者藝評人,現為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任台新藝術獎提名觀察人(2017, 2018, 2021)。主要研究興趣包括當代錄像、行為表演及身體性創作;關注當代加速度政治下的生命政治課題,聚焦於科層機器對身體行動和耗費模式之影響,並且在此基礎之上,持續反思在地藝術理論的生產與擴延。文章散見於《典藏今藝術》、《藝術家》、《現代美術》,以及台新藝術獎「ARTalks」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