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當各界連環揭露#MeToo事件之際,亦開始有藝文工作者於社群網路分享多起性騷擾、性侵事件。立法院也因此社會浪潮,完成性平三法之修訂。
據文化部於2022年3月所發佈的「文化藝術事業應遵守勞動法規指引」第八點(註1),明確指出文化藝術事業需落實保障文化藝術工作者之性別人權及促進性別平等環境,並有預防性騷擾之發生及提供補救等措施。然而多數藝文工作者處於承攬或委任的非僱傭勞動關係下(註2),實難透過《性別平等工作法》提出救濟與申訴程序,若要尋求「正義」,只能進入《性騷擾防治法》的訴訟程序,加深受害人發聲之困難。
為求突破現況,臺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以下簡稱藝創工會)在第三次勞動調查的框架下,再加入性別平等調查的項目,尤其聚焦藝文界性騷擾與性侵經驗的收集。

數據下的殘破現實
本次性平部分的問卷結構主要參考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於2018年所實施的「文化領域性別意識與人權環境實際問卷調查」(註3)及日本一般社團法人日本藝能從事者協會2022 年進行的「藝能/藝術/媒體業界的騷擾實況問卷調查」(註4),就事件被害者、加害者、協助者、目睹者以及聽聞者五大類別對象,進行問卷群組進行調查,依次回答包括加害者的行為樣態、事件發生的地點場合、與加害人的關係、事件發生時間以及事件後之處理情況和個人影響;並整合我國常見與法律實際認定的性騷擾樣態、諮詢從業藝文工作者之經驗想法,設計本次研究問卷。

以此方式設計之「臺灣藝術工作者性別平等與勞動情況調查」問卷,於2024年6月至7月間開放填寫,最後共有944人填答。其中性平事件的被害人,計有162人,占比約17.2%。女性受害人數遠遠大於男性、加害人身分以「前輩」占比74%最高,而僅有36.6%的被害人向外求助,曾尋求協助的受害人亦表示有65%的加害人未受到懲處。
填答者所回應最常遭遇、目睹或聽聞的性平事件樣態,以言語性騷擾(87.1%)為主要類型,再者則是趁人不及抗拒的觸碰(27.3%)、敵意環境性騷擾(22.3%),及跟蹤騷擾(12.1%)。由於本題是複選題,其亦可包含自身遭遇、曾經目睹或聽聞的經驗,值得注意的是猥褻行為(5.2%)、性侵害(3.1%)的出現頻率,在遭遇性平事件當事人的填答者部分,性侵害約有15位(1.59%),遠高於2022年全台的性侵害事件發生率0.073%。(註5)

性騷擾背後的權力結構與旁觀者壓力
以上調查報告結果,實未脫出於我們在調查前的預測狀態,卻更細節地藉由數據揭示了藝文工作領域的性平問題,並再次展現性騷擾和權力結構的關係。「權力不對等與權勢間的相互保護」、「圈內文化與裙帶關係」以及「工作單位與機構的漠視與包庇」,造成受害者難以與之抗衡(註6),也因為這樣的錯綜複雜的權力,連帶形成了「旁觀者壓力」:當看到或得知同儕的騷擾行為時,因為擔心成為目標、對同儕的痛苦感同身受、或因為什麼都不做而內疚、對組織未能防制騷擾行為感到不公正等因素而產生痛苦等因素,形成另一種創傷。
尤其就性平調查報告可見,性騷擾在藝文工作環境實為普遍存在的問題,且藝文工作者因接案和需與多方合作的工作性質,在任何場合皆有可能遭遇性騷擾,然而卻有84.9%填答者回應於工作期間未曾參加過性別平等或勞動權益保障相關課程——這意味著,性騷事件之所以頻繁在藝文產業發生,與性別意識及教育不足密不可分。當工作者缺乏足夠性平知識,除了無法保護自己,相關工作人員也容易忽視這些問題,導致性別歧視與騷擾行為的持續蔓延。種種處境也加深當事人與旁觀協助者的受害意識落差,增加協助者行動時的自我質疑與難度。
「取消」作為非中心化的權力擾動
就旁觀者壓力主題,工會邀請有協助性平案件經驗的跨領域研究與政治行動藝術家李紫彤,與「我們先是人」系列行動計畫成員李橋河,於2024年9月21日舉行之調查報告系列講座:「性別視角下的藝文勞動現場:現狀與困境」中深入交流。
李紫彤就自身經歷,特別提出加害人利用權力優勢控訴被告人之「針對公眾參與的策略性訴訟」手法:有權勢者利用訴訟,讓批評者難以忍受訴訟過程所需之勞力、時間、費用等成本而放棄批評與指控。這樣的操作下,勝訴與否不是原告的主考量,更重要的是讓受害者或吹哨者成為被告而心生恐懼、身心俱疲,最終放棄原本的言論和主張。也連帶製造寒蟬效應,影響公眾的應援和參與。最常見的便是提起誹謗訴訟,如演藝圈#MeToo中,黑人陳建州對大牙的法律操作。
曠日費時的訴訟,也使非僱傭關係的藝文工作者只有《性騷擾防治法》可以依循時產生困境。因此也令人思考取消文化的可能性:然取消是現在唯一可行的方法嗎?取消加害者會不會反而傷害其所屬團隊的勞動權?「取消」後就沒事了嗎?
就當日與談,兩人表示:性騷擾的發生實因為權勢不對等,所以「取消」是以降低消費的方式去擾動現有的權勢結構責任,企圖藉由減少消費降低加害者影響力,是有政治目的的經濟行動。因此,取消文化實呈現無法正當問責的現有制度:因為現有性騷和性侵因為舉證不易,令受害者難以得到有效的法律判決,因此才會透過非中心化、非國家手段的「取消」方式。
李橋河也特別提醒:談論取消時一般大眾很容易混淆對象,譴責機構、國家單位不能隨便「取消」。然給予獎項和補助的國家單位和創作者非消費關係,不能用取消的概念來談,不給予獎補助並不侵害創作自由與基本人權。當創作團隊受加害者牽連而「被取消」時,因依合約向加害者或相關場館求償。
是以,取消文化仍是有必要的手段,而「知道為什麼取消」更是關鍵,讓討論發生,而非避而不談,才能帶來更多的思考與行動,並針對正確的對象究責,不落入權力裙帶的迫害結構。此外,若要落實「藝術性平零容忍」,則需要更完整地建制性平機制,無論是透過公正第三方或是法源,也才能更正當地問責。

在調查之後
涵蓋調查報告的數據與現實困難,一方面業界需落實性別平等教育、建立身體界線的工作守則,另一方面也期待能處理性平問題的第三方公正單位產生,以強化保密申訴機制和提供多元支持。而主管機關亦須增訂性別平等防治措施的指導原則,並針對藝文補助的撤回機制,明文規定施行方式與確保母法,才能有效處理性平事件,又不損及加害人以外工作者的勞動權益。
性平事件背後錯綜復雜的權力關係,實亦揭示藝文環境勞動現有困境與仍需有更多法源保障,更深刻提醒要建構一個安全友善的業界環境,著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註1 根據《文化藝術事業應遵守勞動法規指引》第八點規定:「為落實保障性別人權及促進性別平等,文化藝術事業應推動職場之性別友善、建立無歧視之工作環境,並預防性騷擾之發生及補救。前項勞動權益保障應注意事項例示如下:(一)文化藝術事業應建立性騷擾之防治機制。(二)文化藝術事業應推動職場之性別工作平等措施。(三)文化藝術事業應建立無歧視之工作環境,不得以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性別、性傾向、年齡、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星座、血型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而為差別待遇。」。資料來源:https://www.moc.gov.tw/News_Content.aspx?n=190&s=4136。
註2 就藝創工會2024年「臺灣藝術工作者性別平等與勞動情況調查」,為專職僱傭關係的藝文工作者僅有18%,報告全文可見藝創工會網站:https://artcreator.tw/?page_id=10707&fbclid=IwY2xjawIRO3RleHRuA2FlbQIxMAABHXt3dONDuP8XQ1W_eGT5iW1tf7X8OdCpvQXadl895sszpqIrXDgv3OsNzA_aem_JdaxStp1wd5Ckxb7LXqo9A#page-content。
註3 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문화체육관광부)(2019),《文化領域性別認知與人權環境現況調查結果發布(문화 분야 성인지 인권환경 실태조사 결과 발표)》,
文化體育觀光部(문화체육관광부)。資料來源:https://mcst.go.kr/kor/s_notice/press/pressView.jsp?pSeq=17466。
註4 一般社團法人日本藝能從業者協會 (一般社団法人日本芸能従事者協会)(2022),《藝能/藝術/媒體業界的騷擾實況問卷調查 2022 (芸能.芸術.メディア業界のハラスメント実態調查アンケート2022)》。資料來源:https://artsworkers.jp/category/questionnaire/。
註5 承註2,參考藝創工會2024年「臺灣藝術工作者性別平等與勞動情況調查」,頁26-47。
註6 參考藝創工會2024年「臺灣藝術工作者性別平等與勞動情況調查」,頁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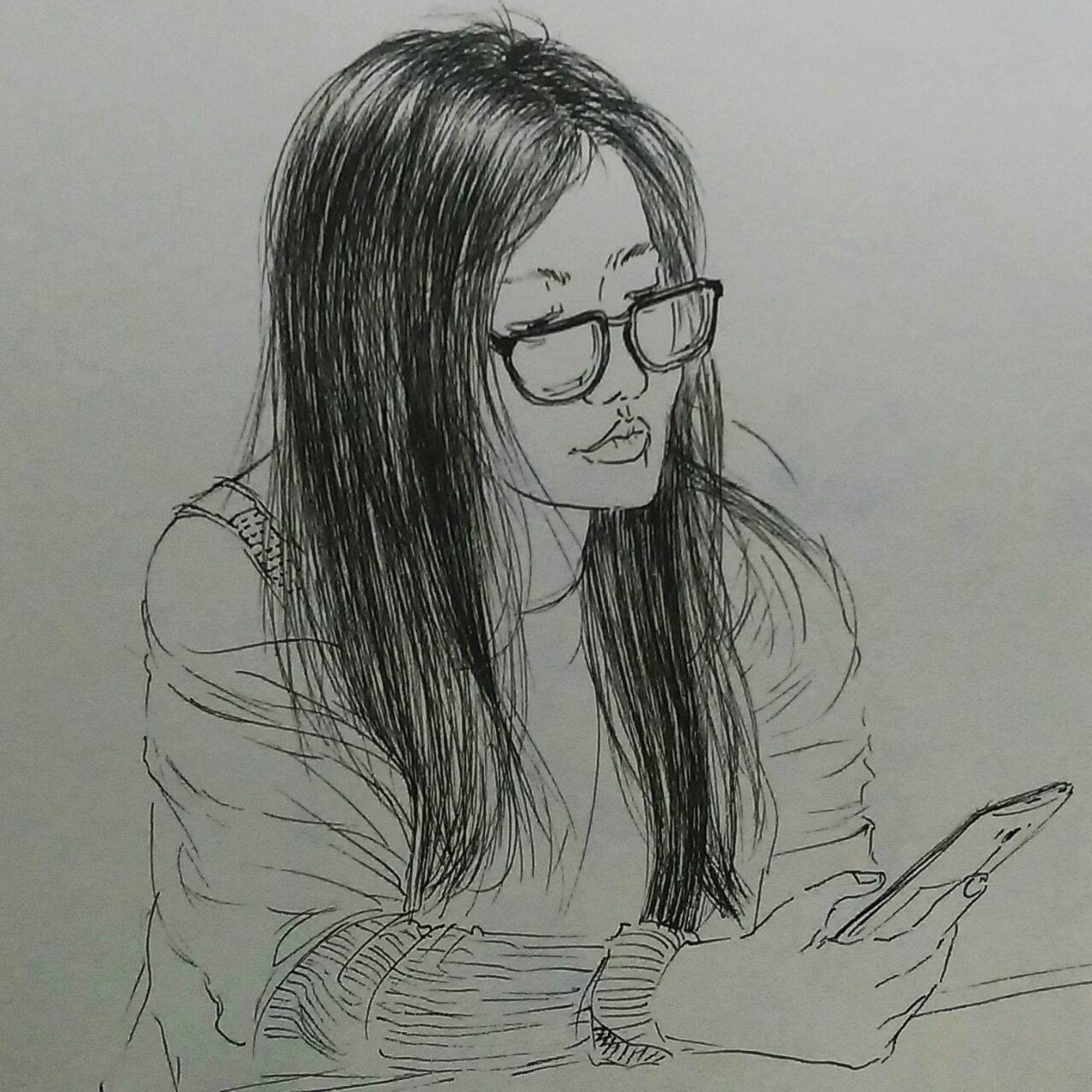 黃馨儀( 2篇 )追蹤作者
黃馨儀( 2篇 )追蹤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