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簡稱「TIDF」)自2014年第九屆起,以「再見.真實」定錨策展精神至今已臻五屆,可謂大大拓展了本地對紀錄片的認識,逐漸跳脫「現實主義美學」與「為弱勢發聲」等既有核心「紀錄—真實」命題。倘若此一任務在十年的實踐積累下或階段性地完成,本文嘗試評析甫落幕的第13屆,拋磚引玉地提問:TIDF乃至當代紀錄片創作,在「再見.真實」之後的下一個十年,或需「再見」何等難題?
之所以認為任務告結,除了因選片對美學實驗乃至紀錄片定義疆界的突破已內化為常態,亦不再於近兩屆的論述中被多所強調;本屆「傑出貢獻獎」得主李道明更在講座上,竄改自身過去為台灣紀錄片定下嚴格、排他、道德戒律式的「寫實情結」、「真實再現」的默契等論點,反向肯定起TIDF策展團隊「帶壞」紀錄片。(註1)從此一令人驚訝的轉折切入,並不意在抹殺其有目共睹的貢獻,而是我們或許可以從這樣的輕言轉向,甚至抹消自身歷史的宣稱中自省:本地紀錄片發展脈絡如何持續處於「滯後」狀態,亦步亦趨地扮演著西方的學徒,並從中再問「再見.真實」的侷限與未竟。
延伸閱讀|是誰在壓抑臺灣紀錄片創作者的主體?從TIDF紀錄劇場《實驗067》試問之

紀錄片系譜的後見之明
當然,若僅以此理解TIDF對紀錄片論述的攪動與擴寫絕非公允,「再見.真實」顯然不只是跟風地單向「告別」真實,更強調透過「台灣切片」與「時光台灣」兩個常設單元,回頭梳理本地紀錄片系譜,嘗試「再(次看)見」(re-encounter)真實中的罅隙。延續而來,本屆「台灣切片」聚焦「1990s以降的女性私電影」,即非為了女性而女性,或為了私電影而私電影,更強調漸進鋪陳所綿延映照出的本地脈絡。(註2)
不過,在2014年首次標舉「再見.真實」精神的TIDF中,其實亦曾同樣透過「台灣切片」單元探討「在攝影機的彼端」。(註3)在當時選映的五部影片中,只有蕭美玲的《雲的那端》(2007)一部出自女性創作者之手,成為兩次策畫間的唯一交集。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執行長王君琦介紹,從TIDF對公共/個人、主觀介入/客觀紀錄的再次探索,可看出「個人紀錄片」的轉向,「在女性創作者的作品中被實踐得最為徹底」,甚至鞏固了此類型如今所擁有的正當性。(註4)

但,「女性」與「私電影」在本地系譜中真的有必然的關聯嗎?「再見.真實」十年前後的首尾對照,或許可再刺激我們省思此一重要回顧性單元可能的視角侷限。如王君琦所論,西方自七〇年代起「個人的即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the political”)紀錄片典範轉移,係受民族誌影像與身分政治影響;但台灣在九〇年代的興起,主要「隨著拍攝器材日益輕巧以及學院開設相關系所」而生,並不全然受女性主義論述啟發。當然,前者可能降低女性投身紀錄片創作的門檻,如此後見之明的詮釋或翻案,也在本單元的百花齊放中有跡可循,卻仍必須對其中的倒果為因戒之慎之:可能抹平了西方與本地間二十年的時差,為此一子類型與特定性別創作者的作品強加模組化的閱讀路徑,進而限縮「女性」、錯估「私電影」在本地的發展樣態,背離本單元的初衷。

另一方面,如此斷代式的歷史回顧,也易陷於為時代概括單一特質的危險,比如六〇的現代主義、八〇的社會運動、九〇的身分政治等,因而在二元論調的選邊站中,忽視盤根錯節的潛伏、過渡與混種。雖然TIDF在相關論述與「時光台灣」等單元中,盡力為線性閱讀的空缺與疏漏提供了相當的補充,但這也提醒著我們:對後進之地的「另類」歷史回顧,或許始終難逃西方所設立的命題框架,充其量只是比西方每個階段轉折晚十、二十年發生而已。這也因此造就了李道明今日的改口,造就了本屆TIDF所欲指認的台菲兩地歷史軌跡的相似等;而除了論述,如同本屆「紀錄x記憶:檔案變形記」所嘗試反省的:技術從來就非中性。若以對檔案影像的批判閱讀再檢視TIDF其他單元的策畫,傳播路徑所隱隱指向的影像技術再殖民,顯然更有待檔案梳理與歷史書寫的反思。比如2018年的「港台錄像對話1980-90s」或本屆的「後國族菲律賓紀錄片」,其實都揭示德國歌德學院在八〇年代的系統性引薦,如何直接形塑當地的影像生產與認識。

紀錄片的「當代藝術轉向」?
倘若「紀錄片」的影像技術與概念定義都與西方有關,我們就不得不小心留意:「再見」所意指的轉向或再發現,是否都只是「再次看見」西方的已見,甚至從中「告別」了本地系譜的不可見?
誠然,我們不能忽視西方紀錄片研究論述早在九〇年代起即刮起「再見.真實」的旋風,千禧年後更頻繁地對「傳統紀錄片」(traditional documentary)發動攻勢,急欲將紀錄片與真實的必然連結脫鉤。近十年大興其道的「散論電影」(essay film,註5),亦如李道明在講座上所肯認的,於虛實概念的重塑下,義無反顧地改寫了紀錄片創作的面貌;但要是這三十年來迂迴擺盪的漸進發展,被遲到地壓縮成以TIDF十年「再見.真實」為代表的紀錄片再認識時,其彷彿僅能重演後進國各式轉型宿命,看似頭過身就過,實際上卻有形無體,甚至愈發長成連自己都認不清的四不像。

而攝影,或許是本地另一個身先士卒的參照。張世倫在去年出版的《現實的探求——台灣攝影史形構考》(2021)中,已警示過此一藝術類型,如何陷入「當代(藝術)觀」的迷思與全稱式的序列階層中;同樣地,倘若TIDF的「再見.真實」未能在模糊的宣稱中,釐清「本地傳統」與「西方當代」的進化論思維,紀錄片的認識與創作實也正重蹈著攝影的覆轍:為了被納入當代藝術而迎頭向上,急欲擺脫「侷限在紀實手法」、「不夠當代藝術」,卻未能針對「本質進行有意義的質問與反芻」。(註6)
從本屆TIDF所選映的競賽片,我們確實看到大量張世倫所稱之「形式語言的挪用、操演與模仿」,美學實驗方法的普遍性追求卻與內容多所斷裂,概念先行地深陷當代藝術創作的範式套路中。許多影片看來更像是計劃型創作中的一環,指向背後更為複雜的議題,「紀錄片」彷彿僅是其藝術創作的部分,或作為一理所當然的展呈工具,少見對媒材形式選擇的必要性——亦即「為何是紀錄片」——提出有力的證明。創作題旨的企圖、牽涉的背景資訊、過程的研究調查皆愈發龐雜,卻未必反映在最終的影像成品中。難道紀錄片不需要如其他藝術媒材接受適用性的檢驗,是因為其已「黃袍加身」地被預先賦予了真實或政治的連結正當性?抑或是我們太渴望美學實驗,對其概念與形式的操作輕易放行?

張世倫除了問及「攝影一定要『變成』當代藝術嗎」,也反向再問「當代藝術是否需要攝影」。若我們再次將「攝影」置換成「紀錄片」,思索此一雙生提問,或許會浮現更多複雜性;事實上,西方對當代藝術「紀錄轉向」(documentary turn)的指證也行之有年。比如近期盛大開幕的德國卡塞爾文件展(documenta),自1997年第十屆起即被視為此一轉向的重要開端;(註7)在這二十多年來的各式創作展演、論壇研討會、研究論述書寫等積累下,當代藝術與紀錄片領域已逐漸形塑出一新同盟。
艾利卡.博森(Erika Balsom)與希拉.佩萊格(Hila Peleg)主編的《跨領域紀錄片》(Documentary Across Disciplines,2016)曾系統性地為我們梳理:當代藝術與電影對紀實性的興趣,起自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批評,以及伴隨而來的後殖民主義方法學的修訂。輔以數位影像技術的普及,藝術家愈發從媒介物質主義轉向對世界與實在(actuality)的探求,嘗試將生活經驗透過「再現的」實踐轉化為意義,卻也不放棄客觀誠實的批評必要。當代藝術的動態影像創作進而發展出「紀實虛構」(docufiction)等混種形式的發明,以及對散論式(essayistic)、民族誌式(ethnographic)、檔案式(archival)與觀察式(observational)等策略的挪用,為深陷大眾媒體與後現代主義雙重夾殺下的紀錄片傳統,延伸至新的體制脈絡與美學可能的領域擴延。(註8)

不過,回頭檢視本地語境,當代藝術與紀錄片的邊界消融,顯然尚未來臨。或者說,我們僅看到後者為脫離傳統窠臼,單向地積極展開「當代藝術轉向」;縱然近幾屆TIDF有幾位主要活躍於當代藝術領域的創作者參展或獲獎,如陳界仁、高俊宏、你哥影視社,以及本屆的許哲瑜等,(註9)但他們的現身彷彿只作為少數代表,障眼法般地證成紀錄片影展的當代藝術傾向;這樣的納入實際上更像是權力資源的分配,而非美學問題的碰撞。幾年下來,「台灣競賽」單元中來自當代藝術圈的外來特例仍然是特例,與本地紀錄片創作生態間的落差也顯而易見;另一方面,當代藝術展演也未必因此開始接納紀錄片創作的滲入,除上述跨界案例,紀錄片導演近年只有黃信堯曾獲邀參與「2018台北雙年展」。雖然我們確實在本地當代藝術創作的田野熱、檔案熱、議題熱中,看到越來越多紀錄方法的使用,但它們或許會被稱作「錄像」,而非「紀錄片」。
紀錄片的「話語空間」?
如此的涇渭分明,顯然是TIDF的非戰之罪,更深受本地美術、電影、紀錄片養成教育及美學論述(aesthetic discourse)等斷裂的影響,難在短時間內一筆勾消。但這也提醒著我們,領域從來就無法說跨就跨。奧奎.恩威佐(Okwui Enwezor)在第一屆「柏林紀錄片論壇」(Berlin Documentary Forum,2010)中即撰文指出:紀錄片與當代藝術各自的「話語空間」(discursive space)實存差異。(註10)兩者的敵對除可見於他所策劃的「第11屆卡塞爾文件展」所引發,且或許延續至今的——「紀錄片是否為藝術」——熱議。
這樣的差異出於對媒介特殊性(medium specificity)根深蒂固的認識,進而形塑出當代藝術的建制與納入排除機制,亦即張世倫所分析的位階關係。紀錄片若要超越新聞媒體報導等既有領域連結,雖勢必得致力找尋新的可能論述空間,但是否一定得服膺於當代藝術的建制?攝影或可再度作為借鑑。在恩威佐引用延伸羅莎琳.克勞斯(Rosalind Krauss)〈攝影的話語空間〉(”Photography’s Discursive Space”)一文中,她回顧十九至二十世紀原被用作地理調查功能的攝影,在被放置美術館、博物館展示閱讀後,如何為論者極力賦予基因上的必然性,驗明其脫胎自繪畫的美學傳統血脈;克勞斯以提摩西.奧沙利文(Timothy O’Sullivan)的攝影為例,反駁這般「彰顯藝術自主性和理想化、特殊化歷史(藉由美學論述構成的歷史)的話語空間」,無論之於影像生產或接收,皆不同於其原先流通於公共領域的展現方式——立體攝影術(stereography),原所強化的是對縱深式「視野」(view)的聚焦,而非攝影被連結至風景繪畫後,在展覽空間中所突顯的「展覽性」(exhibitionality)。(註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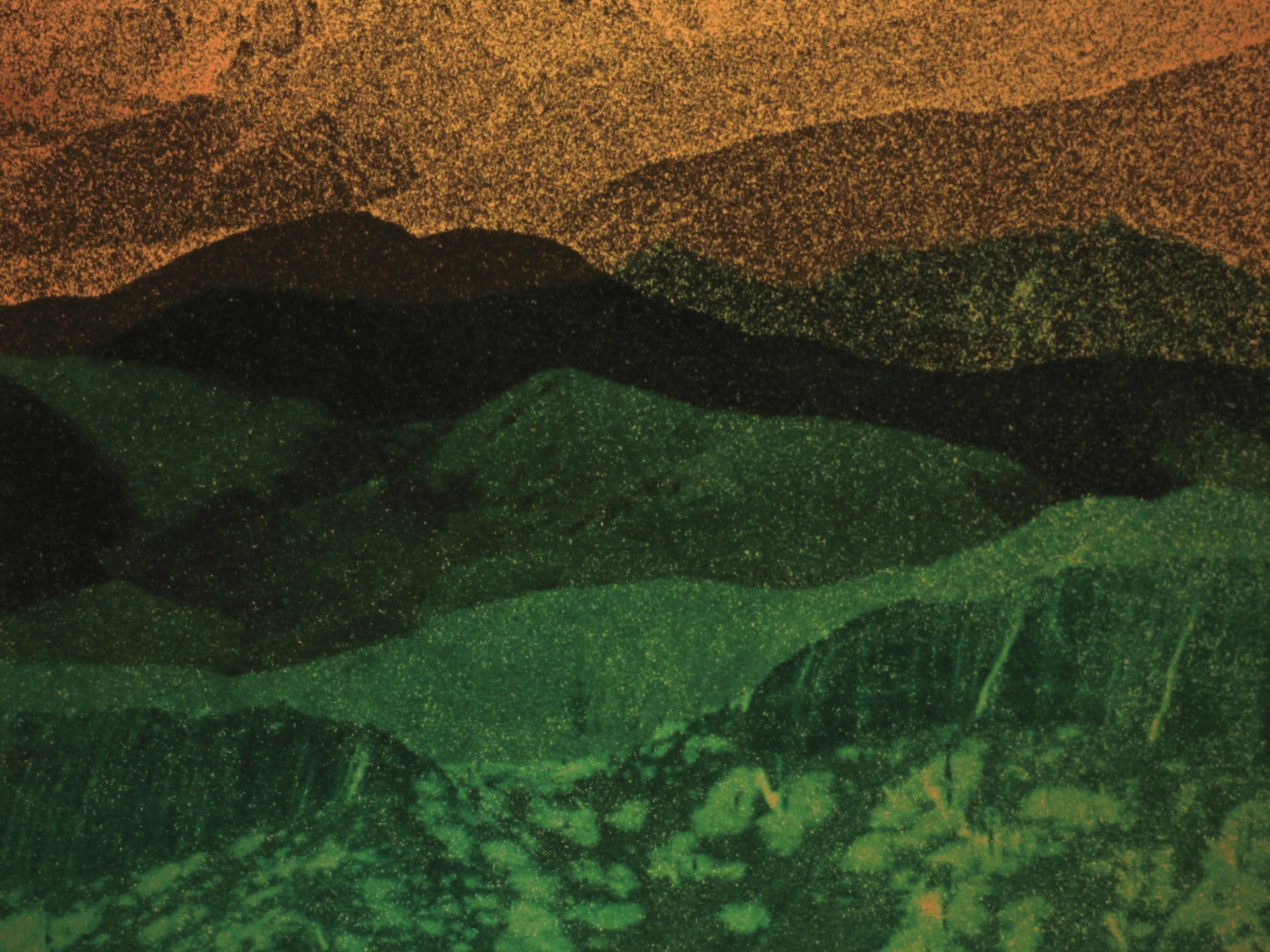
有趣的是,立體攝影正是電影放映裝置的前身,兩者都將觀者置於隔絕狀態中——他們在觀看時動著眼睛而非身體。若以此回頭檢視TIDF,「紀錄片」是否也接棒「攝影」,在取得藝術合法性與價值的路上,正歷經著話語空間的轉變,而逐漸開展出自身的歷史重構?無論是紀錄片的「當代藝術轉向」抑或當代藝術的「紀錄轉向」,是否都逐漸由美術館展覽空間的「展覽性」思維所主導?在紀錄片與當代藝術的交會下,這些不再重視時延、篇幅愈發輕薄短小、方法更為簡單直接的影像創作,還適合繼續沿用「影展」形式在「電影院」中播映嗎?如未能像本屆選映的其中兩部最佳的新片——《earthearthearth》(Däichi Säito,2021)透過底片實驗打造電影院沈浸式聲光體驗,《永無黑夜》(There Will Be no More Night,Éléonore Weber,2020)召喚觀眾集體見證視覺機器的軍事使用——TIDF持續以實體影展容納與展映的必要性又究竟為何呢?

本地紀錄片在影展與商業映演體機制建立之外,其實走過小型放映會、電視、街頭、錄影帶、美術館、展覽空間、線上平台等各種形式場域,其實從來也就非只為電影院而生。平心而論,TIDF近年已多次嘗試以展覽策劃(比本屆如「時光台灣:1986-1991『百工圖』系列精選」)、紀錄劇場、現場電影等形式回應此一問題,並極力思索電影院展映對檔案的激活可能;(註12)但從常規的選映看來,多數影片其實並未將觀看方式納入創作思考中,彷彿其在各種空間展映都可得證。倘若紀錄片愈發脫離影展或電影院展映的邏輯時,TIDF除提供競賽的資源獎助進行引薦外,或許更需要策展思維對其進行論述與調度。


紀錄片的「議題導向」?
當然,這些問題不會僅因展呈方式的轉型而迎刃而解。我並不意指紀錄片必須在電影或當代藝術展覽的兩極擺盪中擇一安之,更非期待透過任一方的話語空間來重塑紀錄片的媒介特殊性。如上所述,紀錄片在新聞報導、電影、大眾媒體、當代藝術間掙扎拉扯、碰撞互滲,其話語空間本即隨著時代變遷不斷在變動。換言之,在影像的分類與領域愈發難以區辨之際,TIDF顯然不能只再憑藉著「影展」形式,與本地舉辦的錄像藝術展、實驗電影展區辨差異,而更迫切必須面對:究竟「紀錄片」的核心判準為何?這個問題在「再見.真實」的英文名「Re-encounter Reality」中,似乎指向了「現實」(reality)。(註13)但在本屆TIDF的選片中,「現實」的複雜性卻有逐漸被「議題」的「人道主義凝視」所取代的跡象,不禁令人懷疑:「紀錄片」今天之所以還能被稱作「紀錄片」,難道是因創作的「議題導向」嗎?

從近五屆TIDF所突顯的「亞洲視野」單元為例,我們雖可看到策展團隊積極串聯區域內部的政治批判,這樣的政治性卻不見得關乎地緣政治的國際意義,甚至可能同樣帶著去歷史的進步論思維。簡言之,我們愈發看到的,是以西方自由民主價值的無差別套用,肩負正義使命般地對國內政局現況、歷史記憶展開淺薄的討伐,其中充斥各式不假思索的政治正確判斷,單向再確認「進步人權的西方」與「落後獨裁的第三世界」間的二元對立。本屆選映的《給珍的信》(Letter to Jane,1972)中,高達(Jean Luc Godard)那句「誰在拍?為了誰?針對誰?」彷彿言猶在耳。
更具體而言,TIDF所處的台灣究竟在這之中的觀看視角為何?其不同於西方紀錄片影展之處又在哪裡?這似乎也隨著政治局勢的變遷而愈發有定論。近兩屆尤其突出的,是對紀錄片創作之於政治「異議」的「收容」。這樣的言論空間無疑是重要的,卻也讓台灣陷入一弔詭的角色位置——既在地緣關係與發展歷程上親近,卻又非我族類,彷彿以民主轉型成功案例乃至亞洲自由人權燈塔之姿,身兼起西方的亞洲代言人,關照後進國跟上的進度。而無論是前屆的高嶺剛或本屆的菲律賓專題,他們所分享、蘊含對美國與日本帝國主義的批判,也都好似與我們無關。

相對於他們從政治批判開展出適切的表現形式,本屆選映的處理政治議題的新作,常相反地藉時下流行的形式語言,單向地說明或完成紀錄的政治目的。其中,多部廣受好評的作品擅用「重演」等方法,對事件現場乃至歷史記憶進行「事後」重塑。我們雖欣慰紀錄片創作不再侷限於現場的見證紀錄,卻也顯然不能只憑藉此一時空距離認定其反身性,甚至必須警覺之中所顯露之更為深層的「現場」執念。
比如勇奪本屆三項大獎的《憂郁之島》(陳梓桓,2022),透過「重演」嘗試對話三段香港歷史——文革、六七、六四與九七,卻未停留於對自身歷史形塑的單向認識。導演在鏡頭前指導著年輕抗爭世代,將自身經驗投射至扮演的角色中。於是,在主流意識形態的後設詮釋下,歷史證言或事件紛紛始讓人聯想起時下政局,並在相互貼合下,證成了感性的時代延續;儘管該片也確實捕捉到被重演的被攝者,在行過千帆後,對當下展現出不同層次的困惑不解,可惜的是,創作者回避了歧異觀點的開展,反而更在乎讓這些仿佛時代局外人般的歷史代表,去理解、撫慰與哀悼當下。正因歷史的再次現身在此全然指向了當下,為其服務與背書,影片在大費周章的歷史回返後,反而更顯時空的斷裂,不但不互為辯證,甚至好似除了「憂鬱」的統稱外,全無相關。畢竟,本片所展示的是:唯有「歷史」需要且能夠透過重演,進行真偽的後設驗證;但「當下」無論是抗爭或法庭現場,卻都如片末堅定的宣言或凝視鏡頭般不容質疑,彷彿它們即是命定的、最後通往的絕對真實。


「重演」雖可供我們檢驗記憶的建構,卻不必然等同歷史意識的保證,兩者不應被混為一談。另一部在「台灣競賽」單元獲獎的《事件現場製造》(許哲瑜,2021),延續藝術家的創作脈絡,以「重演」關注影像技術之於記憶的虛構,但在將題材對象進一步推向高度政治性的歷史事件「江南案」之際,創作者卻未就大歷史與自身(為何回返)、乃至現實政治與數位掃描等影像技術之間的關係展開充分討論。王柏偉對藝術家致穎「總在春光乍洩時」(2021)一展的評論,或已為我們預示了《事件現場製造》的盲點,亦即「以『意義的理解』為基礎的『(人類)意識』不再足以支撐影像敘事中所有『行動』的完整意義,因為有些『行動』是機器所生產出來的。」(註14)本片雖不至於落入傳統紀錄片的再現窠臼,但其透過敘事的偏離與重演的落差所嘗試處理的,還是止步於對「現實後台」/「歷史背面」的再揭露,人物事件本身所蘊含的敘事與符號,指向先行的轉型正義批判追討,經驗性作者主觀的意義生產掩蓋過機器感知對記憶術的反省。
延伸閱讀|《事件現場製造》:與許哲瑜、陳琬尹展開台灣集體潛意識的一次巡弋

紀錄片的「不確定性」?
《事件現場製造》的英文片名「The Making of Crime Scenes」(製造犯罪現場),也恰好指向了我認為當代紀錄片所正面臨的問題——創作愈發接近一場明確、精準設計的「預謀犯案」。一方面,這或許跟紀錄片生產的藝術建制化有關:創作者在面對一次次企劃、提案、工作坊、獎補助審核、創作陪伴等流程後,將紀錄的目的性越辯越明。其中,最矛盾諷刺的莫過於,紀錄片還天真地以為自己正在向當代藝術創作的曖昧性取經;博森與佩萊格即反駁,紀錄片不應該畫地自限,將對傳統紀錄片稻草人式的攻擊,與當代藝術實踐的創造性與反身性相互對立起來,從而忽略自身傳統之於其與現實的關係、之於價值判斷或是之於自我建構的參數,從來就是充滿雜質、論爭與不確定性的。(註15)

而這也正是本屆「紀錄x記憶」等單元所展示的「檔案影像」,之所以可為紀錄片創作提供源源不絕的活泉的核心:正因檔案永遠有著待挖掘的多義性,或可如《後現代韓國》(Post Modern Korea,李泰雄,2021)橫向連結KBS電視台海量素材一般地拼貼對話;或可如《三分鐘——超展開》(Three Minutes – A Lengthening,Bianca Stigter,2021)縱向考古三分鐘旅遊紀錄一般地逐格檢驗等;但,當鏡頭轉回經驗世界時,我們卻很遺憾地從TIDF中看到,紀錄片創作者們似乎不再滿足於現實性的效力。像《浪跡自由》(Soy Libre,Laure Portier,2021)這般願意單純試探拍攝與被攝倫理及張力的作品,已越來越難能可貴。在這部對弟弟出獄生活的紀錄中,創作者展現的是對被攝者、觀眾乃至不可測生活本身的信任。當其讓渡自身的主觀經驗後,弟弟開始取代拍攝位置、自我記錄,甚至逐漸脫離鏡頭的凝視與關係的束縛,成為生命的主宰,而難以再被掌握,留給本片一種未完成,卻也因終將不可觸及而無需完成的狀態。


這樣關係性的互動角力,其實也正是本文開頭談及的「私電影」,在本地所為我們留下的重要遺產之一。但本地論述是否始終過度強化個人經驗的特殊性,使其停留於一次性神話而無法被參照,或進一步方法化與理論化?(註16)更甚者,在紀錄片的「當代藝術轉向」下,這仍會被我們肯認為當代的美學形式實驗嗎?TIDF在「台灣切片:1990s以降的女性私電影」單元中,特別收錄台灣女性影像學會與另一種影像記事於2019年策劃的「從汝浮波瀾:台灣女性實驗電影切片」自成一格,或許已暗示「實驗」想像的特定與排他——主要以晚近西方影像實驗方法,切割與覆寫本地潛藏的紀錄與實驗匯流;而本屆另一部或許會被歸類是「私電影」的作品——「亞洲視野競賽」獲獎影片《我們一無所知的夜晚》(A Night of Knowing Nothing,Payal Kapadia,2021),從前段個人的書信私紀錄,鋪展至後段印度各地學生運動的現場見證,則已為我們證明:公/私、現場/事後、紀錄/實驗、真實/虛構、客觀/主觀等各式二元對立,或許無需強制消弭或交融,而可透過創作者漸進的位移相互共振與辯證,並彰顯出所有斜杠前的、過去被視為傳統紀錄片的特質所內含的強大力量。


誠然,這些二元對立並非具有絕對的標準或方向性。博森甚至進一步分析西方當代藝術的「紀錄轉向」,業已宣告客觀真實的強勢復返。在她對「觀察式紀錄片」(observational documentary)的提倡中,(註17)雖也同「散論電影」強調為觀者創造協調性的時間與空間,讓相異性與不可測在時延的相遇中持續發生,卻逆反其所帶起的主觀影像操作、旁白論述或虛構重演等方法在藝術語境下取得的優位,(註18)更重視以鏡頭為基礎的捕捉,所能產生的非編碼力量,強調對忠於而非操控、問題化而非宣稱的現實(而非真相)捕捉,可重新喚醒我們對世界既有紋理的關注。博森突顯攝影機非人的、無意識的行為與世界相遇的重要性,連同前述王柏偉所提示的「人機共作」,或許都將是數位時代下,當「人類的感知不再是意義生產的第一個接觸面」時,(註19)紀錄片創作所必須面對的課題。

倘若我們不希望走回現實主義的傳統老路,卻也不樂見其一味地向當代藝術傾斜,紀錄片究竟還有甚麼可能性?從鄭明河(Trinh T. Minh-ha)1990年「沒有紀錄片這種東西」(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documentary)的宣稱開始,紀錄片此一「分類」(category)、「類型」(genre)早已在在被取消。(註20)無論是柏林紀錄片論壇視紀錄片為「批判方法」(critical method),或博森與佩萊格將其上升至一種「態度」(attitude);(註21)乃至王柏偉近期評論邱誌勇策劃的「鏡像・映像:80後的當代影像藝術」(2022)時,所嘗試重探台灣集體性、內部生成的「攝影意識」;(註22)都昭示從媒介特殊性的束縛中破繭而出,重新將紀錄片置放在「影像」、「視覺文化」乃至「文化生產」等脈絡框架下理解的必要。TIDF在「再見.真實」後或許顯然也必須重新叩問:對一個紀錄片影展而言,「紀錄片」究竟指涉什麼?方能逃脫當前紀錄片自我擴張卻難自我辨明的迴圈,避免陷入本地文化藝術發展常見的、唯西方是問的錯亂進步史觀中:轉身躍入遲到的後現代,並渴望躋升至當代,卻尚未真正認識自己的現代。

註1 李道明曾在〈臺灣紀錄片的美學問題初探〉一文中,提出此處列舉的論點,並疾呼紀錄片創作者共同思考「如何不會為了新形式而忘了紀錄片的本質與目的,如何不會對真實世界進行偽造、扭曲、干預或甚至重新創造,如何保持誠實的態度進行創作」之目標。詳見:王慰慈主編,《臺灣當代影像:從紀實到實驗 1930-2003》,台北:同喜文化,2006,頁72-76;另外,這樣的說法其實也與TIDF自身的歷史有所出入,其實早在「再見.真實」之前,第三屆與第四屆策展人王派彰與其帶領的「影像運動電影協會」,即已對本地紀錄片認識進行「破壞」。參見: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20週年之2】破壞,才有更多可能!——專訪第三、第四屆TIDF策展人王派彰〉,《上報》,2018年03月19日。(檢索日期:2022年5月25日)
註2 關於漸進鋪陳的本地脈絡,參見:童詠瑋,〈【2021TIDF】從疫情時差下的紀錄片時效性,再探類型化與正典化外的策略:回顧與評論第12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放映週報》第694期,2021年6月30日。(檢索日期:2022年5月25日)
註3 除了《雲的那端》,2014年另外選映的四部男性導演作品分別為:吳耀東《在高速公路上游泳》(1998)、楊力州《我愛(080)》(1999)、黃信堯《多格威斯麵》(2002)、沈可尚《築巢人》(2012)。縱然中間兩部或許不全然可被歸類為「私電影」,但它們同樣關注類近問題意識;2008年,聞天祥在國立臺灣美術館同樣以「私紀錄片」為題所策劃的「私.Me時代:我和我…」,亦選放了《我愛(080)》、《在高速公路上游泳》兩片,而黃信堯則以另一部《唬爛三小》(2005)參展。在當時展映的七部紀錄片中,創作者性別分佈則為五男二女。
註4 王君琦,〈「個人即政治」:談一九九〇以降的台灣女性私電影〉,《Fa電影欣賞》,第190期,2022,頁63-65。
註5 此處的翻譯參考自:王柏偉,〈致穎「總是春光乍現」展覽作品中的散論特質(上)〉,《ARTalks台新銀行藝術文化基金會》,2022年1月31日。(檢視日期:2022年6月1日)
註6 張世倫,〈結語|反思「當代」〉,《現實的探求——台灣攝影史形構考》,台北:影言社,2021,頁479-486。
註7 美國著名藝術史學者琳達.諾克林(Linda Nochlin)亦接著論證「紀錄模式」(documentary mode)對2002年「第11屆卡塞爾文件展」的成功主導,及其如何重新定義「藝術性」的衡量參數。詳見:Linda Nochlin, “Documented Success,” Artforum, September, 2022, pp. 161-163。
註8 Erika Balsom & Hila Pele, “Introduction: The Documentary Attitude,” Documentary Across Disciplines, Cambridge, London: The MIT Press, 2016, pp. 10-19.
註9 這裡所列舉的當代藝術領域創作者並非單向地移植錄像與紀錄片作品,各有對媒介與展映空間的思考,礙於篇幅暫不贅述。
註10 Okwui Enwezor, “Documentary’s Discursive Spaces,” ed. Hila Peleg, Bert Rebhandl, Berlin Documentary Forum 1: New Practices Across Disciplines, Berlin: Haus der Kulturen der Welt, 2010, pp. 9-15.
註11 Rosalind E. Krauss, “Photography’s Discursive Spaces,” The Originality of the Avant-Garde and Other Modernist Myth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6, pp.131-150;轉引自:同上註。
註12 參見:童詠瑋,〈現場的再發現:第十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現場電影」之林強場次〉,《放映週報》第640期,2019年2月23日。(檢索日期:2022年5月25日)
註13 這也是張世倫認為當代藝術「無法迴避來自『攝影』及其歷史的幽靈召喚之因」。詳見:同註6,頁481。
註14 王柏偉,〈致穎「總是春光乍現」展覽作品中的散論特質(下)〉,《ARTalks台新銀行藝術文化基金會》,2022年1月31日。(檢視日期:2022年6月1日)
註15 同註8,頁17-18。
註16 經驗與紀錄方法可否被複製或延續,也是吳耀東在《Goodnight & Goodbye》(2018)與《站在那裡》(2021)中所嘗試處理的問題。
註17 博森所鼓吹的「觀察式紀錄片」不等於「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並未重蹈歷史的覆轍,將現實的再現效力無限上綱。詳見:Erika Balsom, “The Reality-Based Community,” e-flux Journal, Issue. 83, June, 2017。(檢視日期:2022年6月8日)。
註18 在「散論電影」對紀錄片創作的強勢主導下,我們仍看到許多創作者忘卻「主觀性」其實是由作為作者的「我」與作為觀眾的「你」相遇溝通、互相決定與塑造的。
註19 同註5。
註20 Trinh T. Minh-ha, “Documentary Is/Not a Name,” October, vol. 52, Spring, 1990, pp. 76-98.
註21 同註8,頁18。
註22 王柏偉,〈在現實主義的攝影意識之外〉,蔡昭儀主編,《鏡像・映像:80後的當代影像藝術》,台中:國立臺灣美術館、國家攝影文化中心,2022年5月,頁122-139。
本文部份內容首刊於:〈紀錄片的“當代藝術轉向”?:童詠瑋談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ARTFORUM中文網》,2022年7月12日。原文網址:https://www.artforum.com.cn/film/14081。
 童詠瑋( 52篇 )追蹤作者
童詠瑋( 52篇 )追蹤作者藝評人、獨立編輯。關注橫跨視覺、表演、影像與數位藝術等領域。曾任《典藏ARTouch》編輯、絕對空間展場經理,參與《Fa電影欣賞》、《藝術觀點ACT》執行編輯,書寫另也散見於《典藏.今藝術》、《臺灣數位藝術網》、《放映週報》等平台。紀錄片研究論文曾獲世安美學論文獎。現主要研究旨趣為影像理論、左翼文藝、媒介研究、媒體行動主義等。E-mail: tungyungwei@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