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自2010年代上半葉之後,藝術創作的社群正產生新的重組,不僅如此,在地社群也在創造屬於自己的藝術創作。在都會區的大場館時代之外,這些社群創生藝術往往是以環境與生活中的某些特定性作為共同體,而不限於族群或創作範疇。
〈社群創生藝術:部落、創作營、藝術節、藝術村、劇場、工寮、實驗場〉以上下兩篇的篇幅,組織七位書寫者,訪問十組創作社群的集結者與團體,整理出五個命題,作為思考社群創生藝術方法的敲門磚。在上篇裡,我們將重點介紹「創作營之後的社群化載體」與「介於創作與策展之間的精神共同體」兩個面相。
【聚焦花東創作社群新網絡】的其他專題文章詳見:
導言:聚焦花東創作社群新網絡
社群創生藝術:部落、創作營、藝術節、藝術村、劇場、工寮、實驗場(上)
社群創生藝術:部落、創作營、藝術節、藝術村、劇場、工寮、實驗場(下)
花東藝文空間,抽樣與現況 (2016-2023)
重航海洋的文化行動——造船作為一種方法
園區流標了,然後呢?文化中介組織如何救花創?

一、創作營之後的社群化載體— 森川里海藝術行動、Makotaay生態藝術村
如果說「創作營」是2000年代至2010年代花東地區重要的創作生態培育方法的話,那麼自2010年下半葉開啟組織的藝術季與藝術村,則可視作從創作生態進一步社群化的載體。不同社群有各自的組織樣態,而近年來將實踐場域擴延至花蓮縣豐濱鄉磯崎、新社、復興、貓公、港口與靜浦部落的「森川里海藝術行動」,與延續「洄瀾國際藝術家創作營」(簡稱洄瀾創作營)的駐村能量並逐漸往外擴散社群的「Makotaay藝術村」,是其中兩個值得關注的例子。
森川里海藝術行動包含交替發生的「森川里海藝術季」與「森川里海藝術創生行動」,其中一位策展人為節點共創負責人蘇素敏,具地方誌出版、另類空間的創立經驗,另外一位具創作背景的王力之,曾受邀參與2005年洄瀾創作營,並因此成了港口部落的媳婦,留在部落推動社群藝術至今。
2018年的森川里海藝術季,是林業保育署花蓮分署自2016推動「森川里海平台」之後,逐步從「米粑流濕地裝置藝術季」轉型。蘇素敏認為,藝術季需與地方居民的主體性並進,在外顯的藝術節慶活動之餘,需要有扎根的社群藝術動能參與。藉由王力之投注部落文化與藝術教育的經驗,團隊6年來共邀請了33組藝術家和工藝師。「在進入部落之後皆需先向部落學習,才開始進行創作或材料實驗,並將經驗反饋給部落。」
這些動能的基礎來自團隊持續地口訪田調,迄今訪談50位耆老,記錄近百種材料的文化知識,復振和紀錄手藝。在今年台灣文博會「臍帶之地—與山生活」展覽中,他們呈現了藝術行動6年來的方法與成果。
蘇素敏將藝術季視為「依據當地的需求與議題,進行的軟性社會革命。」她認為,唯有跟地方緊密連結、理解現場的複雜性並有機調整行動,才是藝術季的本質。而作為長期在部落生活的創作者,王力之則認為,像是為了捕鰻苗而改良工具、創造歌謠的生活技術,即顯現部落傳統早已充滿創造性的文化技術,「而這就是藝術創作的起點。」(文/陳晞)

在歷經30年的還我土地運動,花蓮豐濱鄉Makotaay港口部落的阿美族人於2020年10月陸續從國家手中收回祖先的土地。此地地主大多是藝術工作者,某種程度也承襲著過去「洄瀾創作營」的能量,希望把藝術種進土裡,「Makotaay生態藝術村」便於該年成立。每週地主們會固定自發性的開會,討論可能發展的計畫,去找到最貼近土地的生活模式。
成立初期,他們曾舉辦「tamita kita走吧我們」藝術行動,邀請許多藝術工作者,花費七天的時間由長濱行腳至港口部落,並進行創作。過程中,沿途遇到的人、文化、材料都成為創作的養分,也串接起彼此連結的機緣。而今年,藝術村更定調為「海洋年」,承襲著過去幾年眾多藝術家與引路人的耕耘,透過藝術行動串連起花東沿岸貓公(Fakong)、港口(Makotaay)及靜浦(Cawi)三個阿美族部落的文化歷史與海洋知識,再邀請長濱及都蘭部落等各地的舟船來到此地匯聚,以身體實際行動,來實踐遺失的海洋文化。
Makotaay生態藝術村另一常態性交流活動是駐村。不同於其他駐村單位,Makotaay不設定駐村主題,不要求提出完整計畫,反而希望創作者透過感受在地自然、人文所帶來的養分以發展作品。他們認為,如果預設目標太明確,會錯失流動帶來的可能性。也因特殊的駐村模式,來到此地的藝術工作者們,時常會組織工作坊、共同田調、訪問、彼此互助。
總的來說,Makotaay生態藝術村因其獨特的成立背景與經營方法,從一次次的藝術行動中,逐步創造不同社群交流的可能。今年更與學校及建築師合作,建造符合自然景觀的三組建築,作為未來藝術與文化教育的工作場所。主事者之一的那高.卜沌(Nakaw Putun)表示,因為與土地夠貼近,所以更清晰看到傳統文化消逝與環境被破壞的樣子,「我們只好努力透過文字、影像,將經驗與知識紀錄、保留下來。」(文/陳思宇)

二、介於創作與策展之間的精神共同體—兒路創作藝術工寮、林介文
有別於大部分藝術或表演團體,2015年由東冬.侯溫成立的「兒路創作藝術工寮」(以下簡稱兒路)實非以特定展演形式為發展目標,而是以太魯閣族文史與生活場域等為核心,開展不同的運作與學習模式。相較於面朝某種當代藝術的舞台或目光,兒路側重的委實是更強的在地關係。
這樣的實踐模式與東冬個人的生命轉向有深刻連結。2016年,東冬接靈成為太魯閣族傳統社會中的「巫醫」(Smapuh),他的創作也開始一如巫者帶有的社會連結性,從早期的踽踽獨行,轉向社群性的命題。2016年,兒路開始正式駐紮在銅門部落,從這一年開始,他們每年透過不同的研究工作與田野活動,創造出以太魯閣族、銅門部落為主的藝術景觀。包括為了讓部落文化不被外來業者壟斷詮釋而開辦的小旅行《巴托蘭之心.兒路唱故事》、為記錄銅門區不同家族歷史而展開的《「千」徙.銅門》;開始與不同族群創作者共同探討部落經驗的《Phpah藝術聚》,以及在古典與前衛議題的交鋒下誕生的部落劇場《遊林驚夢:巧遇Hagay》等。

然而,除卻這些成果性的陳列,兒路的特殊之處,還在於在這一年年推進之中,漸漸成為某種凝聚精神與情感的培力之地。兒路的成員,大部分是來自不同族群與部落的青年學生,某程度上都是暫離學院系統,進入一個更接近於文化生活的互動時空。故這裡的人際連結,除了工藝傳承、表演學習……這種具象的、物理性的層面,還帶有很強的精神性色彩;尤其是以在地的傳統信仰經驗所擴延出來的各種現象,例如夢境的渲染與儀式的承襲。
潘小雪在〈走出來的路〉(2020)一文中梳理臺灣原住民藝術發展時,曾將過去的藝術時間分為三大團塊(三地門、大港口、象鼻部落),並指出接續其後者,即是銅門部落以「巫師文化」發展出來的跨域階段。事實上,不論是三地門、大港口還是象鼻,皆是發祥於1990年代末期的藝術場域了。也就是說,這一以特定部落場域(及其場域的特定媒材與技術)為核心的發展模式,到了2000年代,似乎出現了為期不短的斷層。2010年代的兒路,的確接續了這個系譜,卻開展出不再以特定的物質傳承作為美學基礎,而更強調某種精神層面共同體的殊異方法,並在這一維度上,觸及許多過往團塊發展無以遭逢的命題,例如信仰與性別。這種差異,也體現出原住民藝術在這兩個時代間的岔路及進展。 (文/呂瑋倫)


以織布為重要創作方法的藝術家林介文(Labay Eyong),除了個人創作外,也組織部落織女共同完成作品。2016年於新城火車站的《織路》,即是林介文第一件攜手30位太魯閣、賽德克、泰雅族的織女,耗時三年所完成的大型公共藝術作品。在今年「南迴藝術季—夢迴南方」的新作《晒海》,她再度攜手年齡跨距超過50歲的台東織者們共同完成。
2020年的展覽「裹山」,使她從創作者身分成為策展人,更具有轉動整個「展覽」社群的實質動能。她以居住地紅葉村山上礦區作為展覽場域,展出15位織者的手工編織織品,透過與地景的交織,顯現太魯閣族群所面臨的迫遷史,與難以拆解的產業經濟議題。隔年的「Mhidaw Qabang曬布節」,她則邀請紅葉部落族人將家中的珍藏織品曬於戶外,形成部落暫時性的跨時空文化地景再現。
不論從集體織布創作、策展、抑或是行動號召來看,林介文所創造的都是一種臨時集結的社群,這種集結脈絡也許可以解讀為從原住民文化蔓延開來的工作方法,它打破我們一般將織品本身視為最終成品的觀看習慣,轉而從成品去回看到背後組織社群的運作,以及透過這個集結所打開的對話關係網絡。 (文/陳思宇)

 陳晞(Sid Chen)( 134篇 )追蹤作者
陳晞(Sid Chen)( 134篇 )追蹤作者藝評書寫與研究者,第13屆國際藝評人協會台灣分會理事長,曾任典藏雜誌社(《今藝術&投資》、《典藏ARTouch》)社群暨企劃主編。目前關注異質性的創作與勞動,長期研究繪畫性與敘事性等命題,對於另類文化和視覺語言的迷因混種亦深感興趣。文章散見於《典藏ARTouch》、《CLABO實驗波》、《端傳媒》、《非池中藝術網》、《Fliper》、《ARTSPIRE》、《500輯》、《藝術認證》、《歷史文物》、《新北美誌》等。
E-MAIL |sidtjh@g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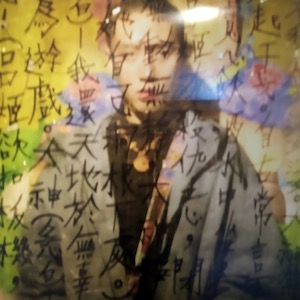 呂瑋倫(Wei-Lun Lu)( 8篇 )追蹤作者
呂瑋倫(Wei-Lun Lu)( 8篇 )追蹤作者策展人、藝評人,關注原住民藝術、後殖民與性別理論研究。近年策劃包括「后古事紀:當代原住民變裝表演叢像」、「情山色海:酷兒.原民.祕密史」、「母神的備忘錄:武玉玲個展」等展覽。
 陳思宇(Sih-Yu Chen)( 151篇 )追蹤作者
陳思宇(Sih-Yu Chen)( 151篇 )追蹤作者藝術研究與書寫者。典藏雜誌社企畫編輯與Podcast《ARTbience藝術環境音》製作統籌。關注音像藝術、跨域製作以及文化環境。文章散見於日本媒體《artscape》、《典藏ARTouch》、《CLABO實驗波》、《藝術觀點ACT》、《Pulima link》、《歷史文物》等。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碩士。E-mail: sihyu0322@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