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幅舞女歌唱圖談起
執筆寫作本文之際,我手邊剛收到熱騰騰出爐的精彩攝影集《台灣綜藝團》。攝影家沈昭良頗具巧思地給予這本書宛如七彩霓虹燈一般的絢爛外盒。取出攝影集,映入眼簾的是一幅輪廓質樸、線條靈動的舞女歌唱圖,出自藝術家於某輛舞台車之側所攝下的圖像,原作者如今已不可考。然而,這幅不知出自哪位無名畫師之手的鮮活圖像,不僅適切地提點出《台灣綜藝團》所欲勾勒的常民生活百態及其充滿生命力的文化樣貌,同時它也再次提醒我們「創造力來自民間」這個基本道理—猶如沈昭良一貫的攝影姿態,不卑不亢地引領我們直視自己腳下的土地,透過其長時蹲點式的專題性拍攝,繼而獲得深入理解台灣社會某一剖面的嶄新視角。

沈昭良│台灣綜藝團(圖/藝術家提供)
就此而言,誠如黃建亮在訪談〈世紀末台灣的內在風景〉中的結語所言,台灣攝影史確實需要具有創造性的「作者」。(註1)因為若非攝影家見人所未見的主題設定,我們不會在折疊油壓式舞台車上重新發現這個漂流在綜藝團五光十色的背景之後,充滿異質符號組裝的絢爛圖像世界;若非攝影家與其他民俗攝影先行者紮實的踏查實踐,則攝影史很可能就只會充斥各種在學會與沙龍攝影文化籠罩之下,千篇一律的競賽照片。無論從美學表現還是歷史檔案的角度來看,面對台灣婚喪喜慶文化的生猛綺麗,以及伴隨宗教祭儀而來的各式民俗活動的豐富氣味、色彩、動態、細節,民俗攝影的記錄暨展呈形式曾有過許多的轉折與(尚待分梳的)內在論辯。龔卓軍近期在他積累兩年研究成果的專文〈影像的佔領.交陪的抗拒:信仰與民俗的攝影史辯證〉中也倡言,當代的民俗信仰紀錄形式已從傳統偏於靜態的保存與檔案建置,走向更為主動的知識建構和文化生產的「後紀錄形式」之再發明/再創造。(註2)而從論述倡議到具體展演實踐,則落實成「近未來的交陪:2017蕭壠國際當代藝術節」裡,他與幾位不同世代攝影、影像創作者之間的合作對話。
「民俗」的死而復生:跳出重複性的美學操演
民俗攝影不是沒有其內在危險。譬如1970年代隨著鄉土文學論戰而起的文化尋根意識與主體性思辨,雖然推動了一整代知識分子與文化人對「鄉土」與「民俗」的熱烈凝視。但在隨之而來的1980年代裡,我們也看到它逐漸演變成一系列僵化、流俗、樣板化的視覺陳套。特別是在台灣喜好辦攝影比賽的怪異風氣下,「民俗」與其他諸如風景、花卉、城市夜景等各式主題一樣,成為一種重複再重複的攝影類型。攝影者們往往只是在比賽或祭典期間,進行相近構圖、主題、風格的美學操演;許多參賽作品多是捕捉一些鞭炮煙硝的瞬間、家將臉譜、信眾膜拜之神情、寺廟的斑駁老牆等畫面。這類形式化的鄉土意象不僅將「民俗」定形為一種重複性的視覺知識,它也同步瀰漫在省展系統,成為繪畫、水墨等其他媒材之美術教育中揮之不去的僵固母題。就此而言,攝影家一方面要照顧到民俗活動對象本身既有的文化紋理,避免去脈絡化地框取其中的行為、器物、儀式或圖像,使攝影淪為武斷任意的影像獵奇和編造。但另一方面,她/他又必須就攝影的影像布置(dispositif)、展呈介面、空間設計,乃至於與其他裝置物件之對話性,去挖掘出影像表達形式的當代潛能。能兼顧兩方判準者,實屬不易。

姚瑞中「巨神連線」系列於「近未來的交陪:2017蕭壠國際當代藝術節」展出現場。(攝影/陳伯義)
在「近未來的交陪」裡,姚瑞中的攝影新作「巨神連線」系列在展示上有著獨樹一幟的陳設形式,是他自「海市蜃樓」系列發展出來的「檔案室式」的影像配置法。他雖以民俗活動的中心—神像作為拍攝對象,卻除卻一般民俗攝影中必不可少的祭典、儀式或特寫人物,僅從遠景捕捉這些象徵著「人類欲力」之投射的巨大塑像。這些影像單張看或許無甚稀奇之處,然而當它們以相當的檔案數量配置於整個空間,從而在「視覺總量」上一次提醒觀眾這些塑像座落於全台各地時,「欲力」的總和便如「海市蜃樓」系列中的廢墟總和,令人怵目驚心。此種藉由影像數量給予觀眾某種宛如類型學一般的全觀式配置,也頗能與沈昭良在「STAGE」系列裡,為舞台車進行大量肖像化的普查式檔案建置,產生形式上的對話。

林柏樑「對視」系列展出現場。(攝影/陳伯義)
林柏樑所展出的「對視」系列,一方面是個充滿個人情感的空間裝置,可視為他對席德進—做為其民俗文化關懷之啟蒙者—的致敬之作。另一方面,也可視為他對廟宇建築、雕刻剪黏這一類民俗攝影的創造性推進。台灣寺廟主持者始終缺乏延請專業攝影家進行如日本土門拳一般系列性、專題性攝影的認知,使民眾難有機會透過攝影的視覺轉化重新認識廟宇建築的細節之美。不過林柏樑打開了一扇窗,他將震興宮、慈濟宮、金唐殿等宮廟裡,經何金龍、王保原等剪黏師傅之巧手塑嵌而成的人物造像一一予以獨立特寫式的肖像框取。在輔以近似幻燈片效果的燈箱設置之後,不僅人物造像上的細節紋路盡現,影像本身也呈現出猶如劇場一般的空間感。毫無疑問,攝影家創造出一種重新閱讀台灣寺廟裝飾工藝的影像介面。

林欣怡《第六十九信:第一信》作品影像截圖。(圖/林欣怡提供)
錄像藝術家林欣怡的《第六十九信:第一信》雖然不以民俗活動為題,但她將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施水環所寫的獄中家書空間裝置化的方式,別具巧思。特別是她在展場中設置了兩個從天花板垂降而下的方形木盒。觀眾必須抬頭仰望,才能窺見幽暗木盒內播放的錄像。如此,透過迫使觀眾改換身體姿勢的方式,錄像裝置提點出施水環之弟施至成,當年藏匿於其姊臨沂街宿舍的天花板上那個狹小、窒悶的闇黑空間。對照陳宣誠散置在蕭壠文化園區內的十座浮洲島,嘗試推進攝影在離開常規的美術館空間之條件下可以擁有的戶外展呈形式。前者是閉鎖性的影像裝置,後者是開放性空間構造,一內一外共振出攝影影像之當代展呈可能的探索空間。

陳宣誠散置在蕭壠文化園區內的十座浮洲島之一《請水島》,陳列陳伯義所拍攝的王船祭典請水儀式。(攝影/陳伯義)
帝國/國家與民間:優影像與弱影像之間的競逐辯證
綜上所述,藉由藝術家個人的創造性實踐與美學想像,確實有機會突破台灣民俗攝影傳統的內在枷鎖。這是無論攝影史書寫還是一般性的攝影教育中,依然必須強調個別作者與創造性的根本原因。不過,民俗攝影史的梳理仍有一些待解問題需要理論與研究方法上的集思廣益。
一般而言,「民俗」確實常被賦予相對於「現代」的內涵,因此人們總習慣將之連結至即將失傳的、亟待保存的古老事物;彷彿將之定焦在靜滯的時間裡,比什麼都重要。然而誠如陳佳琦在〈與「行將消逝的」對決:台灣脈絡下民俗相關攝影影像之初步思考〉中反思的:正如民俗學在常民生活中指認何者為「民俗」,繼而構造出一門以「民俗」為名的學問。民俗影像也在相似的操作中,透過不斷搜索可歸屬於「民俗」的拍攝對象,使其做為特定視覺符號和美學表現母題被確立下來。因此,倘若民俗影像(特別是在藝術家/攝影家的創作脈絡中)漸次趨於一種拒絕變動的、浪漫鄉愁式的固定意象時,它便會劃出一道缺乏彈性的疆界,使「民俗」二字禁錮在只屬於過去時光的認知框架裡。(註3)要言之,如果只思考「民俗」所標定的物象,而不去思考它在過去各個歷史時刻—做為文化知識分子再創造、再發明的產物—所起到的批判性意義,那麼我們將犯下一個危險的認知錯誤:忘記常民文化本身也是流動的、與時俱進的;並沒有一種物件或符號能夠獨佔「民俗」的意義。
但國家或帝國的力量,經常令人忽略上述的思考細節,使「民俗」被再現為一種無庸置疑的視覺檔案或鮮明符號。這是因為帝國/國家必然會決定某個文化地域內生產出的大量影像,何者值得留存甚至於被積極推介,而何者又必須從公眾的視野中徹底消失;帝國/國家必然會挑選符合其治理目的與檔案意識的影像,進而建構出其所欲強加、鞏固的代表性視覺文化記憶和影像美學位階。
由此觀之,1940年代日治時期由帝國泛視觀點所支撐的影像(龔卓軍語),如《民俗台灣》與其他依循日本人類學、民俗學與土俗學之調查範式所生產出來的田野圖像,又或者在國民黨來台之後,1970年代英語漢聲《ECHO》雜誌所精緻化的圖文再現,兩者皆可看到帝國/國家力量運作的深刻痕跡。前者,有著殖民者為其治理目的或者凝視異文化的欲望陰影存在。而後者,則有著綁架在中華文化的思想架構下,將台灣民俗轉化為精緻文化外銷品的符碼化隱憂。這兩者,無疑都因為直接或間接受當帝國/國家支持,進而在誕生之初便已佔先地處於影像階級秩序裡的優勢位置。此種優勢影像與費佐(Michel Frizot)在談論影像生產之客觀命運,如何事先決定了其形式、大小、品質時(註4),隱然欲指向的那些未受帝國/國家之力青睞的、屬於攝影生產底層的「弱影像」,並不能等同視之。這些漂流在費佐所言之「諸場域」(家庭相簿、私人文件夾、廣告插圖、報紙……)之間且品質良莠不一的弱勢影像群,恐怕仍是當前攝影史書寫未能探照到的幽暗之地。
因此,順著龔卓軍所述,在攝影史內部的「藝術表現VS.歷史紀錄」之觀看二分體制之外,我們還可再添加另一個二分體制,是未來台灣攝影史書寫(及更大範圍的影像史書寫)必然得嚴肅面對的課題,那就是:(國家、學院)機構化的優勢影像vs.被機構排除在外的弱勢影像。前者,從屬於傳統藝術史書寫模式之下對「個別創造性心靈」的檔案化意識、知識生產,以及相應文化資本積累的一整套話語體系。而後者,則是從屬於史戴爾(Hito Steyerl)於〈為弱影像辯護〉(In Defense of Poor Image)中所述的「弱影像」(poor image)經濟體系。(註5)這是一個在國家機構與學院機制之外,以諸如YouTube、Vimeo、Instagram等網路影音平台和社群媒體之即時分享網絡為表現陣地的龐大體系,一個使用者/業餘者都會自動成為影像之編輯者、評論者、翻譯者,以及(共同)作者的世界。
在過去,我們習慣忽視這塊影像生產機制領地,視之為重複性美學演練與各種定形化視覺母題充斥的影像陳套聚集地;唯有那些勇於朝向差異化感性經驗的少數創作菁英的成果,才值得嚴肅對待與研究。不過史戴爾提醒我們,不應過於簡化地看待這種「讓許多人集體製作與觀看的影像」內潛存的創造力,弱影像並不只是一種大眾化的流俗影像,因為它們同樣構成了當代常民生活的實況。
史戴爾對弱影像的辯護或許帶有過於孤高的「人人皆可從事影像生產」之烏托邦色彩。但我不禁揣想著:如果我們真的相信在文化上對「民間/民俗」的再建構,能夠翻轉過去藝術教育僵化的美學位階(如「美術」與「工藝」之分),並從中孕育一種真正多元而具自反性的寬闊視野;如果對「民間/民俗」的再發現與再創造,不只是為了文化主體性的欲望服務,還是為了從中孕育出一種足以直面當代性的深刻思想暨實踐方法,那麼,重新找出「創造力來自民間」這點的當代意義,讓「文化藝術」的話語權從學院機制內部再次釋放出去,恐怕仍有其必要性。唯有如此,我們才可能真正看見屬於這個年代的民間/民俗影像為何,並從中激盪出與常民生活之間的平等關係。
就此而言,沈昭良在《台灣綜藝團》封面上的那幅舞女歌唱圖仍充滿了啟示性。因為它所象徵的,不就是一場專業攝影之眼與另一無名的民間專業畫師之間無聲的影像對話嗎?
註1 黃建亮,龔卓軍訪談,〈世紀末台灣的內在風景〉,《藝術觀點ACT》,68期,2016.10,頁54-62。
註2 龔卓軍,〈影像的佔領.交陪的抗拒:信仰與民俗的攝影史辯證〉,同前註,頁5-13。
註3 陳佳琦,〈與「行將消逝的」對決:台灣脈絡下民俗相關攝影影像之初步思考〉,同前註,頁20-21。
註4 Michel Frizot, A New History of Photography (Konemann UK Ltd, 1998), p 11.
註5 Hito Steyerl, “In Defense of Poor Image,” e-flux Journal #10, November 2009. ◎www.e-flux.com/journal/10/61362/in-defense-of-the-poor-image/(參照時間:2017.0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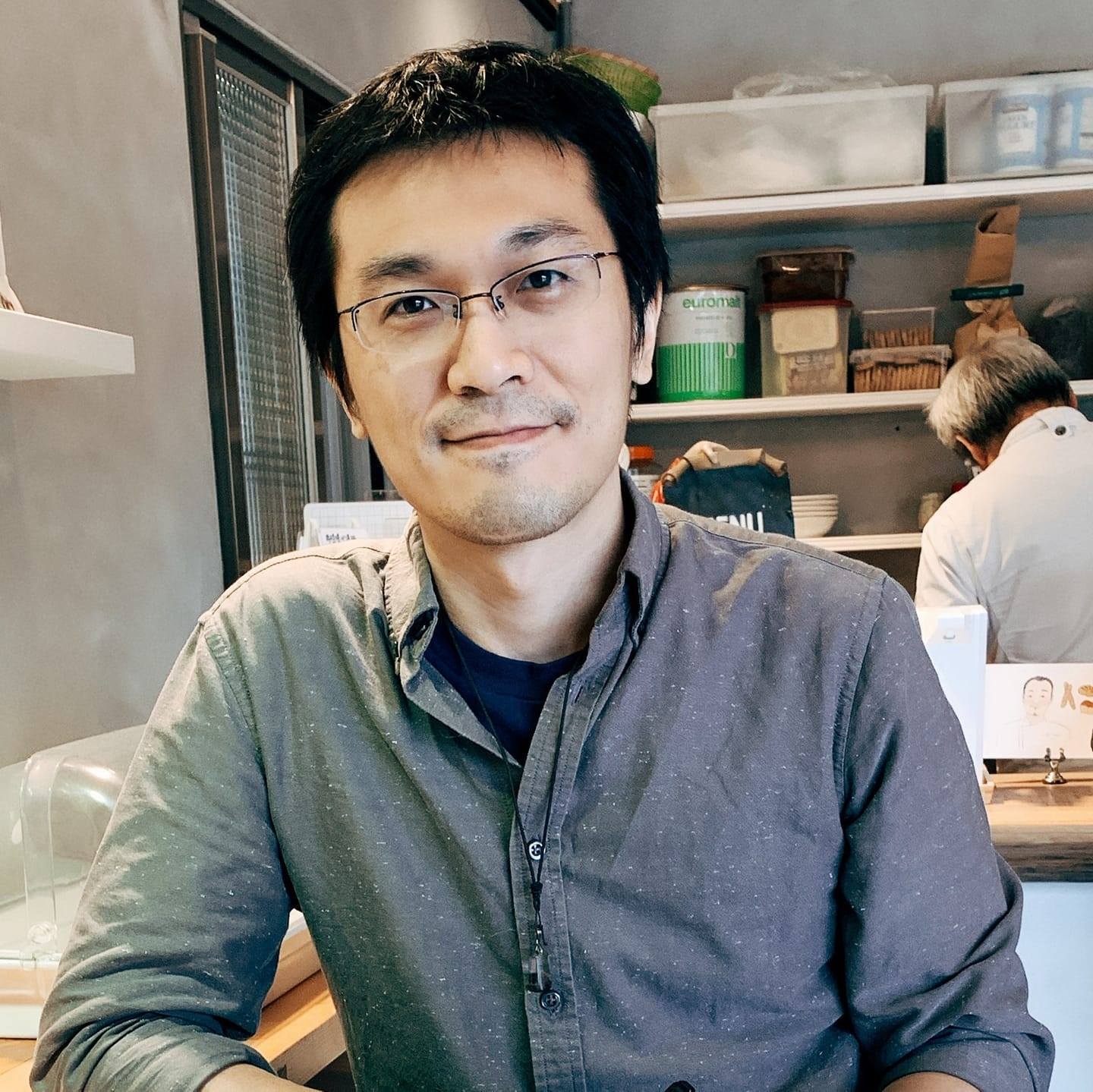 王聖閎( 13篇 )追蹤作者
王聖閎( 13篇 )追蹤作者藝評人,現為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任台新藝術獎提名觀察人(2017, 2018, 2021)。主要研究興趣包括當代錄像、行為表演及身體性創作;關注當代加速度政治下的生命政治課題,聚焦於科層機器對身體行動和耗費模式之影響,並且在此基礎之上,持續反思在地藝術理論的生產與擴延。文章散見於《典藏今藝術》、《藝術家》、《現代美術》,以及台新藝術獎「ARTalks」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