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0年代開始,西方人類學界就吹起一股「原住民酷兒」的研究風潮。自此,從人類學,到藝術、文化研究的領域,非二元式的性別論述,甚而成為北美原住民解殖意識與行動的節點。這一現象,稍後也在與台灣原住民有親緣關係的南島語系島國發酵,除了研究者的著力,還高度源於當代創作者的推展,成為近年全球原民酷兒論述的重要場域。(註1)也就是說,自上世紀末期,這一關於非二元、非典型性別的研究現象,開始成為世界性趨勢。非常有趣的是,作為某些人口中的「南島母親」、在族群研究上一直頗具動力的台灣,在這一張全球「原酷」的圖譜中,卻是高度缺席。
不過,與南島部分島嶼相似的情況是,近代,在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的發展,確實對此現象做出了補遺。我曾於過去多篇文章指出,2010年代的原住民當代藝術是一個「酷兒現身」的時代(註2) ,這些在過往的民族誌、殖民文獻乃至於藝文發展中空缺的性別視角,開始透過出生於1980年代的創作者,拓展出原民族群認同與酷兒性別認同的闡連可能。風流水轉,原住民藝術也在這個時候,隨著世界思潮的演進,成了從全球到地方皆受到極大關注的母題;這一世代的原民酷兒藝術家,依緣亦開啟了許多突破性的發展。然而,進入2020年代,新一世代的「酷兒」們如何迎向這個劇烈滾動中的巨輪?他們與稍早的前行者之間有什麼關係?出生於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發芽的1990年代、成長於它爆發的2010年代,這一場域中已稍有基奠的「原酷」發展,是他們所承接的遺產、捷徑、還是僵局?
「酷兒困惑」的承續與差異
我曾指出,2010年代原住民當代藝術場域的「酷兒現身」隨即迎來的卻是並未與之對應的、漫長的評論空缺,其中一個原因,是在此一「現身」初期,併之而來的,其實是一種非常難以快速被指認、釐清的「酷兒困惑」情感。這樣的一種「困惑」狀態,一大部分源自於酷兒主體在彼時極度性別二元化的族群文化與藝術語境中,不可能不感覺到的衝突與困境。以1980年代出生的東冬.侯溫(Dondon Hounwn)與林安琪(Ciwas Tahos)為例,他們的第一次現身,即分別以一個尖叫抓狂的陰性身體、與被膠帶封死的嘴巴,騷動了過去原住民藝術場域中已充盈許久的文化肯認氛圍。這樣的酷兒困惑,打開了顯然迥異於「主流社會」酷兒藝術的開端;它並不止於情慾、身體、變裝等的顯化展現,而是在「族群」與「性別」的拉鋸中,開啟了複雜的認同辯證。爾後,東冬與安琪確實也開始離開這種「困惑」狀態,進入一個建立酷兒身分正當性的歷程,高度發展至今。

然而,到了2020年代,出生於1990世代的原住民酷兒們,與此造「酷兒困惑」卻並不一定不再相干,甚可能拓展著它的意識與邊界。以太魯閣族的游恩恩(Lihan Umaw)為例,作為一個在部落長大、從小就感受到強烈「性別不安」的孩子,她爾後的人生歷程,都在面臨二元性別身體的轉生。這裡的「轉生」不是修辭,是真實的肉身過程。是以這一過程中的巨大痛楚、壓抑、瀕死與祕密,事實上亦開始把過往酷兒們還能捏著的某種「隱喻」的藝術語境逼近斷弦。當恩恩帶著這樣的身體與性別經驗,轉身面向自己的族群認同時——在祖先的世界裡,有沒有「她」的歷史與未來?在遠古的神話中,有沒有「她」的記憶與遺言?在親緣的連結裡,還有沒有「她」所能接收和給予的諒解跟愛?酷兒的提問,於此走向了一個更尖銳、更難以安頓的處境之中。
恩恩此前的表演歷程正高度拓張著這種「酷兒困惑」的濃度與殘酷。她的演出總有一種令空氣凝結的尷尬,熱舞時不知該不該尖叫、結束時不知該不該鼓掌,一切都懸而不決、未歸類、無解答,她的性別革命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也並不會在任何前行者所拓闢的族群認同路徑中找到答案。

另一位生於1990年代的阮原閩,則如許多原民青年一樣,他們的成長背景已高度混雜了不同族群文化的經驗,他們都是上世紀一整代島內移工的都市後裔。他的族群情感甚而起源於他在網路上「搜尋」自己的族語名字、而找到他的賽德克族爸爸在他出生時寫給他的一封信。他的名字「Siyat Moses」承繼於爺爺,字裡行間,還有那麼多父親的祝福與期待。但阮原閩同時還是一個對自己的原住民文化極為陌生、而且喜歡研究公主跟漂亮衣服的男孩。其實這樣的文化混雜與陌生狀態,與林安琪的背景雷同。不過在阮原閩身上,卻並不一定作用出如2010年代時的濃烈不安與躁動。
在他的作品裡,透過對於傳統服的媒材顛覆、原住民肖像照的性別混淆,創造出一種模稜兩可的原民意象。這種「不精確」的原民樣式,相較於在「酷兒困惑」的不適與不安中扎進母體文化的宇宙裡探途找路,他更像是在早期荷蘭人等殖民者留下的、畫得荒腔走板的原住民圖像裡,找到今天的自己。「困惑」不是一個需要被解決的僵局了,它像被當成事實一樣的被接受。於此,困惑主體並未再給出任何肯認動能,他就是要站在這種邊界之間。這是否會是這一混血世代的其中一種強烈特質?當然,它亦僅是目前為止的發展和觀察而已。

「酷異神話」的授予和變革
無論如何,可以確定的是,出現於2010年代的「酷兒困惑」現象,並不是特定時期的特有現象,而是在這一身分政治的場域中,酷兒主體在面對當代的原民族群認同時,可能永遠會有的一種情感狀態。無論它將被推到更緊迫的界線,或不再被視為一個生命的問題叢結。
另一個有趣之處是,這些「原酷」藝術家們,在面對他們的「困惑」情境時,幾乎都回到「神話」的敘事裡,作為一切探問的開端。在某些2020年代的創作者身上,甚且出現對於上一代前行者的承續。在游恩恩2024年的表演藝術作品《Tnpusu起個圓》中,有兩個關鍵物件,其中之一是石頭。「石頭」在太魯閣族的起源神話中別具意義,因為人類的初祖,就是從石頭中走出來的。但是,在泛紋面族群的諸多神話文本中,這石頭走出的並不只有一男一女,其實還有第三個神靈,然而這第三個靈到底是誰,就眾說紛紜了。在東冬.侯溫的口傳版本裡,這第三個靈最終成了Suling Utux,中文語境貼近「荒野之靈」,祂離開人類界域,創造了未知與混沌的世界。
對游恩恩而言,Suling Utux未明的性別身分、不在二元歸類裡的例外性質,深深吸引了她的目光。在《Tnpusu起個圓》中,她奮力敲開石頭,想要一睹祂的身影與祕密,最後卻只在四處噴發的沙塵與碎礫中留下自己。這是她對東冬口傳神話的援引與敘寫,或許,神話的原述者不一定會「喜歡」恩恩對Suling Utux的詮釋,然而在恩恩的作品中,這一深深吸引著她的神話,本也還只是一個小小的、尚未全然伸展的開端。《Tnpusu起個圓》中的另外一物件,是工地模板。這是恩恩對於去世爸爸的記憶,是她還沒「轉生」前,常常跟著爸爸去工地賺錢的氣味。父親、石頭、Suling Utux,其實交織了三個生命的起源,他的起源,他們的起源,與她的起源,然而起源之後,應當才是故事真正的開始。

阮原閩的《出口Rhngun》從命名上,或許已能猜到它也是一個與泛紋面族群的起源神話有關的作品。只是他所承繼的神話版本,一男一女不是從石中走出,而是從樹中走出,他亦未援用第三神靈的角色,而是混淆了兩位神靈的性別狀態,創造了一對身分不明的先祖,並以原住民過往被殖民者「凝視」下所生產的民族誌肖像情狀,轉印在一件又像男裝、又像女裝,像族服、像和服、又像漢服的寬衣之上。事實上,這些對於神話角色的扮演與性別混淆,亦非常容易讓人想起2010年代的東冬.侯溫,然而他們之間依然有不小的差別,在過去,混雜不明的族群意符其實並不常出現在原住民藝術家的作品裡。「混血」的文化經驗、身體經驗,其實是許多出生於1990世代的原住民主要的生命情境;2020年代藝術場域的特色之一,也包括這種跨文化、跨血統的情感與身體經驗,開始出現在原住民藝術家的創作中。(註3)
《出口Rhngun》的寬衣對面,還有一組鏡面裝置。十數面鏡子上,輪廓隱約的私密肉身,彷彿是兩位初祖在民族誌的鏡頭背後、尋歡求愛的肉體灑遺。我曾多次指出,原住民酷兒所再現的神話文本,常常帶有情色意義。(註4)事實上,原住民的古典神話本就充滿各種對性的奔騰想像,酷兒通常只是將這些封印在民族誌裡的嚴肅文字,重新予命。

陰性身影與滾動中的巨輪
「神話」之所以深深吸引著酷兒,或許就是因為它隱喻性的、液態性的敘事,相較於現代社會、宗教殖民後的二元思維與理性世界觀,有更多開放的、模糊的、未定義的創造性空間。神話其實很「酷兒」。過去數十年,神話被作為當代原住民重新建構族群文化主體性的關鍵,或多或少被賦予了某種現代意義下的神聖意涵,然而從2010年代至今,不論是東冬的Hagay、安琪的Temahahoi,恩恩從東冬處承繼的第三神靈、或原閩性別混淆的人類初祖,酷兒藝術家對於神話的再想像,早已擴充了過往的族群研究學者對於神話的固態詮釋。而且隨世代推進,有越來越「放膽」的傾向。(註5)
綜上所述,這二十年,或許已然可以瞥見在藝術場域中的「原酷」發展,已有其承續性與變革性,出生於1990年代的創作者當然受前行者的影響,然而不同的世代也正面對著不同的時代景況與思想拓延。相較於過去的藝術場域,今天,整體的文化產業其實挹注了非常多的資源與關注在「原住民藝術」的發展上,1990年代出生的原住民創作者,乃至於相關的策展、研究與評論人(例如我),相較於過去,竟已可稍微覺得自己是站在小巨人(們)的肩膀上。我們面對的時代景況之一,就是「原住民當代藝術」早已不是過去主流藝術史邊緣的一支孤花,而是一個可能會由越來越多人結構而成的巨輪。
作為一個被戲稱為「原住民藝術裡的邪魔外道」(註6)的研究者我,對於這樣的發展其實是感到忐忑的;「酷兒」如何航向或抵抗正典、如何成為或不成為這巨輪裡的一顆螺絲釘,或是一個把這輪戳破的釘子,有時連我都不小心在這酷異性與族群性的巨大差異與闡連實驗間走到迷航。不過這是不是最迷人的地方呢?2020年,我第一次策展,想以性別政治的視角梳理原住民當代藝術。但主辦處性質保守,我又小,很多事不敢寫明,就寫「陰性」。後來,策略故,亦不想再閃爍言詞,「原住民酷兒」這至今還是走到哪被碎念到哪的概念才被我搬出,我卻在這巨輪滾動的此刻,又懷想起「陰性」這曖昧不明、又充滿抵抗力量的詞。
我的心裡曾有點擔心,沒錯,是擔心,「原酷」論述的發展終將隨某時期的創作者們航向正典。這有什麼不好,其實我也不知道。但我對「正典」有偏見,我不太相信世上有任何的正典、在實務上可以容納所有的差異生命……不過看著新一世代的創作者,我開始(自私的)感到鬆弛。那些還不是很穩定的身影,還在顧盼猶疑中的姿態。在巨輪的面前(或之中?),我們還是沒答案,前者已遠行,後者未可知。正因如此,一切都還是很迷人。
註1 以薩摩亞或夏威夷為例,原住民酷兒正透過紀錄片、出版、創作等不同的文化行動,高度發展著在地的多元性別論述。其中許多研究者同時也都有藝術創作者的身分。例如2018年出版了重要著作Samoan Queer Lives的Dan Taulapapa McMullin與Yuki Kihara等。
註2 參見拙作〈山海迷障:原住民酷兒的寫實轉向〉,《典藏ARTouch》,2023。
註3 包括泰雅族的黃林育麟(Temu Basaw)、Kagaw Omin等1990年代出生的年輕創作者,近年皆有意識地在藝術創作上聚焦於自己「非」原住民血統的組成部分。這一發展目前很難被收束在過往的原住民當代藝術框架之中,但它應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
註4 我曾在《情山色海:酷兒.原民.秘密史》的策展論述中指出,原住民酷兒的「情色」亦非只是西方哲學語境下的「erotic」,當我們開始重新想像一種前殖民時期的性別世界觀時,它是一種饒富後殖民意涵的解殖行動與藝術策略。「情色」的重要性出自於北美原住民研究者Qwo-Li Driskill,參見Asegi Stories: Cherokee Queer and Two-Spirit Memory,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16.
註5 此言並非意指過去的藝術家作風保守,而是創作者對於古典神話的理解,開始有了差異。相較於東冬的「Hagay」實為家族長輩的口傳神話與過往的真實人名、安琪的「Temahahoi」是泰雅族民族誌中確有的記載,恩恩與原閩對民族起源神話的援用,體現出他們面對經典(甚至是神聖的)文本時不同的想像尺度。不過,這種差異亦牽涉著不同世代的主體所身處的社群處境與文化態度,背後實為一頗為複雜的世代議題。
註6 陳晞語。
本文原刊載於《今藝術&投資》2024年12月號387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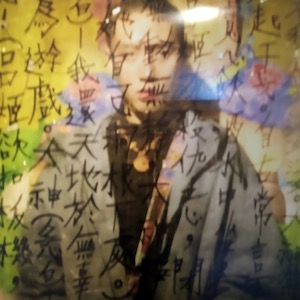 呂瑋倫(Wei-Lun Lu)( 8篇 )追蹤作者
呂瑋倫(Wei-Lun Lu)( 8篇 )追蹤作者策展人、藝評人,關注原住民藝術、後殖民與性別理論研究。近年策劃包括「后古事紀:當代原住民變裝表演叢像」、「情山色海:酷兒.原民.祕密史」、「母神的備忘錄:武玉玲個展」等展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