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為工作方法展示的攝影書
不過在1990年代,台灣的影像創作曾有一段時間不再以這種專題拍攝的路線為核心,也不再固守「紀實」兩字。成長於藝術學院體制內的影像創作者多半不像他們的前輩一樣投身新聞媒體以歷練自己的攝影工作方法,而是積極走向展呈方式更加多元,或者更具挑釁意味的影像、行動、裝置之混合形式。相較之下,沈昭良堅持扛著大型機具進行《映象.南方澳》、《玉蘭》、《築地魚市場》等專題拍攝計畫的創作型態,顯得相當「古典」。(註1)
不難想像會有人提出質疑:如此堅持走在紀實傳統之中的攝影創作,究竟還能帶出多少新意?它是否還具備回應當前社會瞬息萬變之脈動的能力?以及更重要的,在這個Instagram、直播App、社群媒體及串流服務當道的影像消費年代,像沈昭良這樣的攝影家如何抵抗影像總是即生即滅的速食趨勢,提出前所未有的新視界?對此,精彩而紮實的「STAGE」系列無疑是沈昭良的回應,他那帶有人文地誌考察及檔案建置意味的舞台車肖像,從方法到形式,都充分展示出攝影靜照可以具備的當代性。
但相較於已頻繁接受世界各地邀展,且積極參與當代藝術展演的「STAGE」系列,眼前甫出版的這本《台灣綜藝團》或許才更貼近沈昭良攝影工作方法的骨幹。且對照這些年來,台灣當代藝術也正逢一波問題意識與創作實踐方法的轉向,對於歷史的重新敘說、檔案建置、地方性生產,乃至於田調踏查和民族誌書寫,都有日趨深入的探討。而沈昭良堅持長時投入的專題性攝影,恰恰彰顯出一種既能創造嶄新視覺語彙,同時也能揭示具體實踐方略的參考價值。特別是,不同於攝影展必須顧及影像與展呈空間之對話性、觀者動線安排之適切與否等其他考量,因此必然會是較為精鍊的影像選取;攝影書做為「另一個展演空間」更能充分呈現一位攝影家的踏查足跡(註2),以及他/她如何決定與拍攝對象之間的關係距離。其次,讀者也可透過攝影書的編輯方式、裝幀巧思,乃至於紙張磅數及觸感等細節,讀出一位攝影家如何藉由各種訊息和線索來布局他/她的影像敘事,引領讀者主動察覺埋藏其中的政治、經濟、權力、國族等議題面向。對於有心展開視覺性踏查的當代影像創作者來說,沈昭良(以及他時常請益的張照堂)這些在攝影書編輯功夫上投入大量心思的攝影家,其實提供了一條相當具有系統性且立即的學習參照管道。光是這點,就足以構成在數位時代繼續推動攝影書出版—做為一種攝影實踐方法與工作邏輯之完整展示—的重要原因。
兩個女人的目線,與一種端正的凝視
細讀《台灣綜藝團》的裝幀設計,沈昭良選取一個猶如舞廳球燈映射出的七彩炫光做為其外盒。封面則是一幅以螢光紅為基調、造形趣味的舞女歌唱圖。初步觀之,這明顯是為了提示綜藝團文化喧騰熱鬧、光線亮麗的一般性意象。但如此的設計事實上卻是為了烘托內頁從頭到尾皆是黑白靜照,較為肅穆沉澱、引人思忖的一面。透過這種直接的視覺對比,攝影書直接在裝幀形式上巧妙地帶出民間的廟會慶典與婚喪活動的悲歡交合,以及神聖空間與欲望空間總是繁複交錯的特色。
移動式歌舞秀的演出基本上是從無冷場的。為了點出這種「熱」,但又不像「STAGE」系列是以環境空間的繽紛色彩做為核心要角,《台灣綜藝團》通本選取溫潤而細緻的暖調印刷,一方面保留住拍攝現場的氛圍,另一方面又可引領讀者的目光,使之聚焦在這項獨特產業裡的人事物細節上。特別是,綜藝團文化擴及台灣民間社會諸多層面,從廟會、繞境、鄉里聯歡會、地方選舉造勢,到一般家庭的紅白包場合,很難不令人眼花繚亂。因此在影像敘事的編輯上,我們可以讀出沈昭良刻意安排兩條相對鮮明的主線,一是鋼管舞者小燕子和其夫婿結婚生子的歷程,一是孝女文君的工作日常,藉由兩個女人的目線來貫穿常民生活百態。其中,在小燕子的敘事線中尚有個細微的對照:沈昭良刻意併呈她賣力趕場工作,同時又忙於籌備自己婚宴、身著白紗的畫面,勾勒出女舞者穿梭在台前幕後,奔波於他人慶典以及自己生命重要時刻的堅毅身影。而後,再以一張小燕子夫婦的新生兒照片做為轉折,來銜接孝女文君工作所屬的悼亡世界。一生、一死,影像以舞者與孝女個人生命層次的近距離觀察為縱軸,以各種儀式段落、秀場演出中的生命力展演為橫軸,提供讀者宏觀與微觀層次兼備的觀看切面,進而深刻理解綜藝團文化背後的社會脈絡以及欲望結構。
以攝影書呈現的好處,是可以避免過於武斷的敘說,以及帶有明確道德評斷的危險。對於影像與影像之間的潛在關聯,以及線索與線索之間的可能對話,沈昭良留給讀者們許多自行判斷與想像的空間。這也是他攝影創作一貫的基本態度—無論是舞台車還是舞者,攝影家都賦予其端正無比的文化肖像形式,籲請觀者/讀者壓抑妄加評斷的衝動,正眼瞧一瞧自身文化的內在紋理和感性細節。長久以來,這種不卑不亢的凝視姿態無疑是台灣人的自我觀看意識中,最為欠缺的部分。
重探「觀看自己」的修辭方式
可以說,攝影書提供我們的是一種兼具理解彈性和修正力的影像敘事,但它需要相對緩慢且心胸開放的閱讀耐心。可惜的是,在一個習慣被餵養簡單答案、講究感官直接衝擊的影視環境裡,並不容易擁有這樣的耐性。而訊息過量再過量的當代媒體生態,也助長這種日趨淺薄化且難以專心的意識泥沼。於是乎,台灣人的自我觀看意識的修正工程,若不是導向一種異國情調式的文化轉譯,就是只能訴諸「外部觀點」的刺激。前者,往往意味著強勢文化的藝文工作者,挾其產業體制龐大的文化、經濟資本而來,對台灣在地文化細節所做的各種陌生化挪用、擷取。一般民眾經常必須透過這種異國情調的文化視差,才有辦法真正看見自己文化中的美好質地。(譬如,不少年輕人是經由日本動畫導演押井守(Oshii Mamoru)《攻殼機動隊2:無罪》中的廟會遊行場景,才認識到台灣傳統陣頭文化與建築的豐富色彩和造形)後者,則是台灣任何領域創作者的共同宿命—「外部觀點」時常意味著你必須先成為他國文化體系裡被承認的能者,熟練訴說異地的藝術語彙;換言之,先成為台灣人自己也不甚熟悉的一位「異鄉人」,而後你才會進一步被自己土地上的人認同。上述兩者,都無法真正孕育出一種不被文化自卑心態束縛的自我觀看意識。
過去沈昭良發表其攝影書時,伴隨而來的部分即時報導,其新聞下標方式往往也是訴諸他國外部觀點之肯定,以對比台灣人自身的漠視或無知。(註3)這充分顯示影像生產和言語修辭之間的嚴重斷裂;在創作一端,雖已有不少攝影家、導演或藝術家,探索出各種自我觀看的嶄新路徑。但在輿論傳播一端,卻仍未發展出對等有效的修辭策略來適當描述、推介,繼而影響台灣社會看待自身藝術文化成果的方式。總而言之,從狹義的攝影文化評論到廣義的視覺文化討論,台灣社會都有非常長的一段路要走。
優影像身分的兩種抵抗
但這更加突顯出《台灣綜藝團》這種攝影書出版的重要性,因為紙本攝影書的存在至少象徵兩種關乎自我觀看意識的抵抗。
簡言之,讓特定的影像以高精細度的品質、細緻考量的編輯形式印刷出來,而不是透過冰冷的虛擬介面示人,基本上是一種優影像(rich image)的作品化邏輯。影像學者史戴爾(Hito Steyerl)曾於〈為弱影像辯護〉(In Defense of Poor Image)一文中,為優影像的對立面—「弱影像」(poor image)展開辯護。但她主要是為了述明在數位化的影音分享年代,弱影像經濟體系的存在有助於讓影像的話語權重新回到每一個公民手中,而不會被少數權貴階級或者主流影視媒體帝國的產銷邏輯所壟斷(儘管弱影像總是有著內容品質良莠不一的危險)。(註4)但史戴爾較為忽略的是:影像公民並不會甘於擁有弱影像。(註5)以品質更為穩固優異的影像來保存值得留影的事物,或者透過優影像指出值得人們另眼看待、賞析的世界面向,是一種很根本的影像衝動;而攝影家更是經常藉由優影像的創置提出見人所未見的觀看之道,從而打破人們對事物的舊有刻板印象—這正是優影像的核心價值。
就此而言,《台灣綜藝團》所勾勒出的台灣民間社會肖像畫,首先是對國家/官方定於一尊式的文化樣板圖景的積極抵抗。因為由國家/官方出面主導,依其治理目的與檔案意識所選定的代表性視覺文化記憶,往往是一種災難。而其所灌輸的影像美學位階(何者優越,何者低俗),時常就是台灣人無法正視自己文化的元兇。據此,來自攝影家個人意志或民間機構力量支持的攝影書出版—做為一種優影像形式—本身就是關乎自我觀看意識的影像異議。
其次,像《台灣綜藝團》這樣的影像踏查,總是以長期積累的時間跨度,鍥而不捨地深描台灣社會角落。其所匯聚出的優影像叢集有著令人無法忽視的沈重份量。如此縝密的攝影實踐,是對這個影像看過便忘的速食年代的一種緩慢抵抗。但在此,並沒有「專業」與「業餘」的無端對立,因為《台灣綜藝團》的出版既不是為了豎立高不可攀的藝術成就,也不是炫示某種難以企及的奇詭拍攝手法。毋寧說,它只是一種觀看方法的誠摯邀約:
我們能否以這種角度再次審視自己腳下的土地,不必過度自我膨脹,但也無須自我否定?
這是《台灣綜藝團》向我們發出的潛在訊息。再來,就看台灣人如何透過這些影像資產,重新與自己的真實模樣相遇。
註1 郭力昕,〈古典的沈昭良〉,「伊通公園」網站。◎www.itpark.com.tw/artist/critical_data/515/579/-1(參照時間:2017.03.09)
註2 沈昭良口述,龔卓軍訪談,〈文化肖像的凝視舞台〉,《藝術觀點ACT》,68期,2016.10,頁44-45。
註3 譬如:謝孟穎、潘渝霈報導,〈為何台灣人總愛瞧不起自己文化?當「電子花車」成低俗象徵,德國人卻這樣盛讚〉,「風傳媒」2017年02月17日。陳宛茜報導,〈台灣舞台車藝術 這些照片老外看了都說好厲害〉,「聯合新聞網」,2017年02月19日。
註4 Hito Steyerl, “In Defense of Poor Image” e-flux Journal #10 – November 2009. ◎www.e-flux.com/journal/10/61362/in-defense-of-the-poor-image/(參照時間:2017.03.09)
註5 在此,我們以「影像公民」泛指所有運用優影像或弱影像媒介參與公眾事物、對社會重大議題表達意見的社會公民。
熱切凝視紀實的眼
沈昭良《台灣綜藝團》的出版,搭接的是近年愈趨熱烈的紀實影像列車,在此僅列舉數個近例:攝影書出版有蔡明德的《人間現場:80年代紀實攝影》、王有邦的《好茶:王有邦影像話魯凱》、張照堂所編之《影像的追尋:台灣攝影家寫實風貌》,紀錄片有黃亞歷的《日曜日式散步者》,大型展覽則有台北市立美館的「時代之眼-臺灣百年身影」展、高美館的「玻光流影:約翰湯姆生世紀影像特展-鏡頭下的福爾摩沙與亞洲紀行」、國美館的「銀鹽世代-尋找歲月靈光:臺灣攝影家原作展1890s-2015」等。無論是出版、展覽或專題講座策辦,我們似乎不難察覺這波以「攝影史梳理或攝影實踐之回顧」做為思索台灣自身文化社會樣貌的主要介面,從創作端到評議端的討論高峰。繼1980年代中後期紀實攝影在台灣全面盛行的前一波浪潮之後,當前這股熱切凝視紀實、探究檔案的氛圍,似是對1980年代曾經留下來的種種軌跡乃至於遺憾,從思想到行動的再次推進與翻轉。
綜觀而論,當前這輛紀實影像列車所標舉的影像形式,大抵仍不脫現場抓拍、直擊式的黑白靜照,或以紀錄片/動態影像敘事鋪陳議題脈絡的傳統範疇;相關展演活動所觸及的人物,也多是已名列歷史的攝影大家。(某方面而言,這些出版/展演/論壇都在促成台灣空缺已久的攝影史書寫。)沈昭良攝影創作的內核,自然也屬於這條紀實影像美學的香火。其工作方法特別具有一種「掘土者」的特質—執著、踏實、安靜,願意投入大量時間去跟拍、蹲點,與拍攝對象和周遭環境建立起深厚的關係,繼而生產出一個又一個需要無比毅力才可能完成的影像專題。

沈昭良《台灣綜藝團》中的攝影作品。圖│沈昭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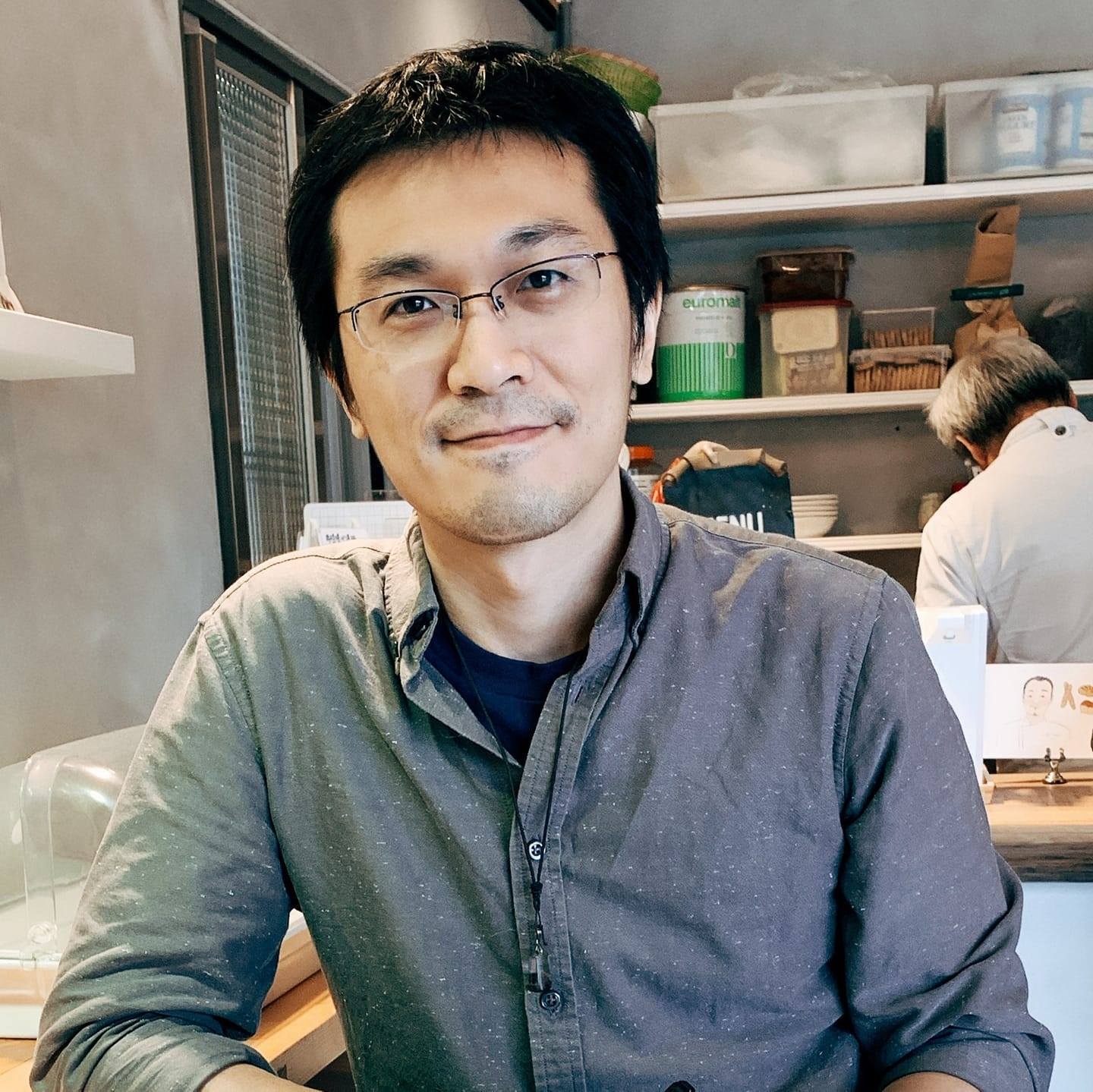 王聖閎( 13篇 )追蹤作者
王聖閎( 13篇 )追蹤作者藝評人,現為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任台新藝術獎提名觀察人(2017, 2018, 2021)。主要研究興趣包括當代錄像、行為表演及身體性創作;關注當代加速度政治下的生命政治課題,聚焦於科層機器對身體行動和耗費模式之影響,並且在此基礎之上,持續反思在地藝術理論的生產與擴延。文章散見於《典藏今藝術》、《藝術家》、《現代美術》,以及台新藝術獎「ARTalks」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