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達文西逝世500周年,手握《蒙娜麗莎》的羅浮博物館,自然早早空出檔期,虛位以待。為了達成在特展中展出達文西所有傳世畫作的終極目標,羅浮博物館還主動向義大利文化部伸出橄欖枝,只要義大利同意借出達文西的作品,羅浮在2020年也會禮尚往來,借予義大利重量級的拉斐爾作品,玉成羅馬舉辦拉斐爾逝世500周年的華麗大展。無奈計畫趕不上變化,義大利新政府後又以達文西畢竟是義大利人,面對如此重要時刻,義大利豈有虛化自己成就羅浮博物館的說法,威脅推翻協議,義法兩方高層只好緊急重開對談。因為歷史紀念不容錯過,但凡是使命或典藏與其關聯的博物館美術館,都會預先籌畫,以求在具里程碑的時間點推出展覽。如今年是台灣文化協會成立百年紀念,就有台灣美術館的「進步時代─臺中文協百年的美術力」、台灣文學館的「百年情書:文協百年」、台北市立美術館的「走向世界:台灣新文化運動中的美術翻轉力」及接下來台灣歷史博物館、北師美術館特展的熱烈響應。
排特展檔期是門藝術,中大型博物館美術館由於展廳多,一年得辦幾十檔展,除了致敬重大事件、館慶或周年等絕無延期可能的展覽外,還有常態、依據館舍發展方向策畫的展覽等等,林林總總。如北美館、高美館每年的台北獎、高雄獎,及北美館、國美館的雙年展都是定時亮相的展覽。國外很獲好評、值得延續的系列、久未碰觸的題材/類型、新研究新趨勢新認可或社會關注的焦點,也是引進或排入展覽的理由。各館且須依照自己過往經驗和觀眾參觀行為決定展覽內容和時程,如美國大都會美術館服裝部門的年度大展通常在五月開幕,自然史博物館的重頭戲多安排在暑假親子團活躍時。有些館是由不同策展人輪流負責企劃;有些館則是以資源或人氣來分配,如一年至少一檔高預算、大卡司的製作,再加一些實驗性質的小品。但具體而言,美術館在排展時既要單獨思考展覽本身,也要宏觀檢視展覽落在美術館內外時空脈絡中的位置及相對應的文化產出。

為了方便俯覽全局,許多館舍的未來工作階段期是以3至5年為基準,慢慢以特展把時間軸線上的月份區塊一個一個填滿。一般來說,博物館美術館的常設展展期長,陳列的絕大多數都是自有現成藏品;特展展期則僅在2至3個月間,籌備時間也可能相對較短。但特展展品常需從其他博物館或收藏家處借得,也就是說,在處理所有相同的煩瑣細節之餘,如找補助、做行銷、出版學術圖錄、設計教育活動、製作衍生商品,特展作業人員尚得負擔借件、運輸、保險等額外的沉重行政。如果是當代藝術家的展覽,有可能在展出時還會加上新創作,不過藝術家手邊一定另有其他計畫同時進行,所以越早開始溝通協商越好,如2009年中國藝術家艾未未訪台,其中一個目的就是為兩年後的《艾未未.缺席》展勘察北美館場地,待雙方達成共識,就能盡快敲定日期、定調展覽。大館的習慣是至少12至18個月前必須確定,媒體宣傳也會跟著啟動,重要藝文期刊如《藝術新聞》(Artnewspaper)或《阿波羅》(Apollo)因此得以在每年年底或年初時,條列並點評世界各地來年的大展。當然,如果真的遇到上級臨時交辦或應變突發時事,就算時間緊迫,在壓縮其他展覽展場或期程的變通下,館舍也多還是能設法擠進新展。如美國肯塔基州的Speed美術館,因是遭警察擊斃的非裔女子泰特(Breonna Taylor)家鄉,即使新冠肆虐,也硬是在 4個月內做出《應許、目擊、思念》(Promise Witness Remembrance)一展,回應「黑人的命也是命」(BLM)運動。不過台灣公立館舍展覽製作、布展,需要上網招標,程序上實在無法太急就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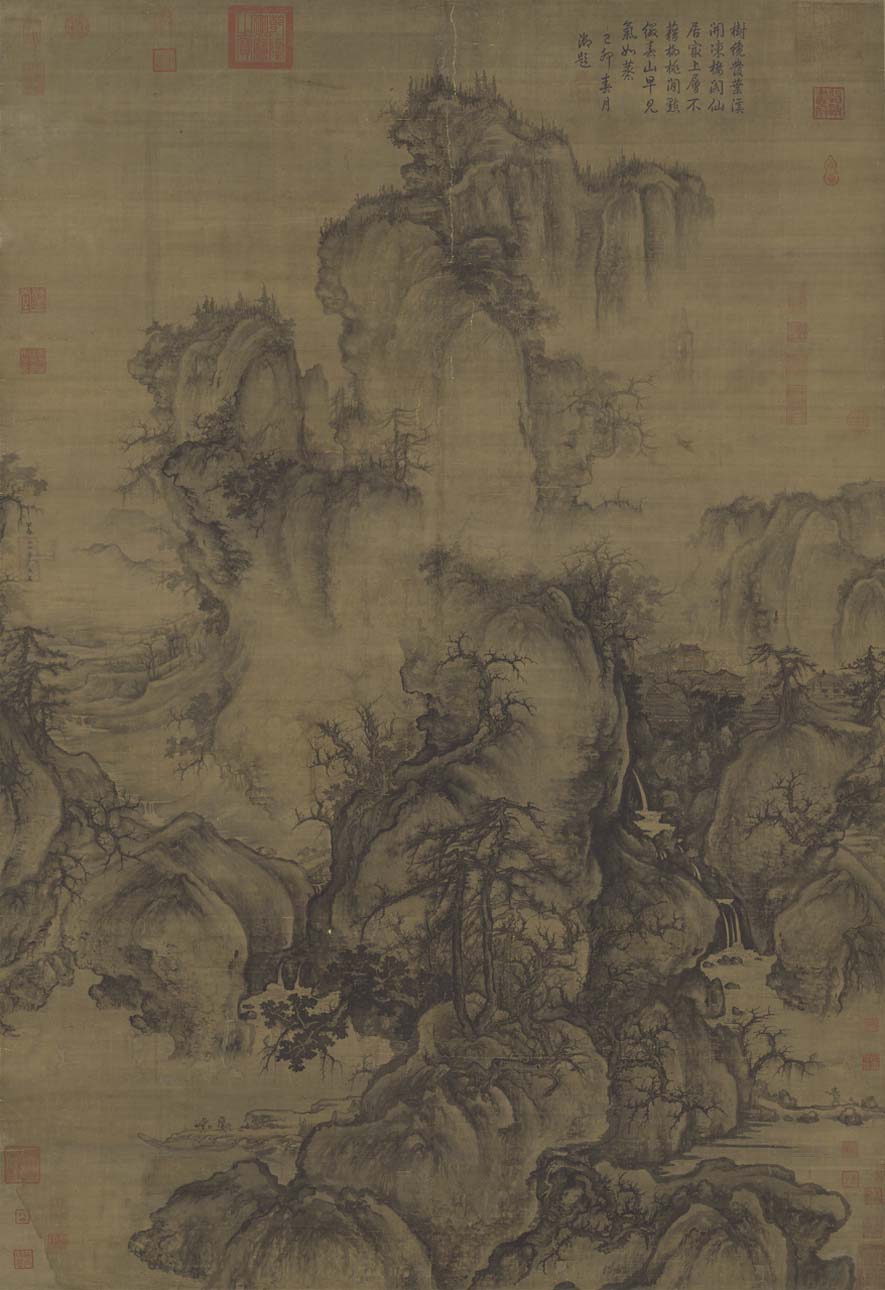
在這漫長的過程中,究竟館方應於何時與乙方簽約呢?教科書的標準答案是:一旦展覽提案被接受,雙方就應在任一方因此產生勞動前簽訂註明各自權利義務的合約。如美國大學藝術學會(College Art Association)的客座策展人雇用指南,是很多學生首次接觸展覽業務的入門參考,指南開宗明義即提醒,必須先有合約再進行實質合作相關工作。亞德里安.喬治(Adrian George)所著的《策展人工作指南》中則說,在收到書面通知或確認基本展覽日期與預算後,就有簽約的必要性,藝術家個展的情況亦同。因為藝術家清楚知道條件與死線(deadline),減少不確定性,美術館展覽「出槌」的機率也會大幅降低,所以合約不僅保障藝術家,也保障美術館。台灣策展人許峰瑞在訪談中曾說台灣現場實務快於官方文書,往往藝術家有進度後才會簽約,積非已久,輿論似乎也普遍認為台灣生態不若國外健全。尤其國外畫廊經紀制度完善,因為畫廊常會先墊付作品製作費用、贊助展覽或藉展覽機會深化與收藏家的關係,展覽順利與否影響其切身利益甚深,美術館面對各方關切,的確更必須循規蹈矩。但事實上,國外美術館也曾有在合約上大意而吃虧的例子。
2006年,瑞士藝術家比歇爾(Christoph Büchel)獲美國麻薩諸塞州當代美術館(Massachusetts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委託創作〈民主的訓練場〉(Training Ground for Democracy)。這件作品是仿美軍實體訓練時用的模擬村莊而做,尺寸規模與一般展覽不相上下,其中包括電影院、兩層樓高的村屋、數個貨櫃等,因為量體巨大,主要構件都是由館員在比歇爾的指示下購入架設,但直至預定開幕日,作品仍未完成,所花費的30萬美金也已遠遠超過美術館預期,藝術家卻因美術館不願持續添購組件,決意走人。麻州當代美術館要求對外展出已完成的部分,滿足大眾對公共藝術機構期待,遭到藝術家嚴正拒絕,雙方不得不法庭相見。美國對著作財產權有縝密的保護,但對著作人格權的討論一向比較少,本案中有關著作人表示其本名或不具名之權利,著作人享有禁止他人以歪曲、割裂、竄改或其他方法改變其著作之內容,形式或名目致損害其名譽之權利等著作人格權議題,都堪稱是《視覺藝術家權利法案》(1990 Visual Artists Rights Act)通過後最具代表性的範例,因此受到藝壇人士和法律學界高度矚目。

但媒體迅即目瞪口呆地發現,此計畫從頭到尾沒有簽訂任何書面合約,以至於到底要做什麼、能花多少,兩造各說各話,毫無交集。比歇爾成名甚早,麻州當代美術館也是美國眾多當代美術館中的後起之秀,僅憑口頭之詞行事,也許是真禮義之邦的表現,在法官眼裡卻顯然是好傻好天真的莽撞,「一個法學院二年級學生起草的書面合約就可以解決今天90%的問題」。習慣金融界凡事照契約走的華爾街日報記者直言無法理解美術館的思維,受訪的館長湯普森(Joseph Thompson)則堅持一諾千金的做法從來沒有造成任何困擾,麻州當代館在過去8年已經和大約800個藝術家共事過,館方相信善意(good will)和真誠(good faith)足以維繫與藝術家的雙向互動,此後也不打算以冰冷的條約取代彼此的默契。
比歇爾和麻州當代館的糾紛,歷經3年纏訟,最終以和解收場。善意和真誠在法律上的主張空間非常有限,但破壞建構善意和真誠的信任卻很容易,更糟糕的是,世上再也沒有比互信更脆弱的情緒。無論是在館內或館外,互信一朝遭破壞,都需要很長很長的時間才能修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