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再以我的生命為基礎,用我的文字建這一小方地,看看,能不能再給你一個中心,好嗎?」
—邱妙津《鱷魚手記》
若說邱妙津筆下的鱷魚是一介於陰性與陽性之間的尷尬存在,自我定義為「不完整的人」,那麼書寫即創造了其嘗試接近「中心」的過渡空間─陰性書寫的空間,在被邊緣與被「中心」排除的境外之地,重新建立自己的中心。
今年下半年度,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策劃了兩檔大展─「她的新電影」及「孽子們的天空:台灣同志電影選」,前者以陰性視野重探臺灣新電影運動和彼時產業中的女性工作者;後者則在同志驕傲月與同婚合法五週年之時,回望臺灣同志影像發展樣貌。2024年,當性/別運動已能以不同樣態在公眾場合上驕傲盛放,重探的意義在於將陰性的目光投向那些曾經被邊緣、混沌不明、被噤聲、無鄉的存在,再次記憶它們走到陽光下被看見與聽見,並建構出自己的中心和家的過程。本文試以「她的新電影」選映之《殺夫》(1984)與《鮮殺》(Fresh Kill,1994),以及「孽子們的天空:台灣同志電影選」選片《私角落》(2001)為例,試論這些影像中某種介於「之間」的陰性特質,如何形成那抵達終點前,個體能夠安身的「一小方地」。

陰性與陽性身體的過渡:《殺夫》
「她的新電影」以改編自李昂同名小說的《殺夫》數位修復版為開幕片,開幕典禮邀請到跨性別工作者酸六再現《殺夫》經典橋段,表演者隨著現場演出音樂層層疊加,將外衫緩緩脫去,身著輕薄如電影主角林市披掛的白色背心。他雙手抱胸,徐緩地感受自己的身體,彷如進入幻境,恍惚間才倏地抬起雙手,揮下第一刀。此時我想起李昂《殺夫》中描寫林市下刀的字句,以及曾壯祥處理此段落的影像手法─那些夏文汐不停重複的、抽格放慢的,彷彿跳針一般的起落執刀動作,如同李昂多次描寫強調林市「彷彿在夢中」的抽離現實感。而眼前表演者那些嘗試感受自己身體的肢體語言,柔緩的觸撫,亦就像進入潛意識、夢境一般。是以,從文本、影像,到現場再現的林市這些遲滯、如夢一般,往自我內在探的身體,就是一種陰性的過渡狀態。
李昂小說前半,花許多篇幅細細描寫陳江水殺豬:他如何下第一刀插進豬仔的喉口,到不斷重複拔刀、下刀的放血動作,以及最後俐落開腸剖肚,掏出所有內臟的屠宰過程。而在這些屠宰前後,「林市更相信自己仍置身夢中」。如置身夢中的恍惚感,與林市親眼所見的屠宰場景以及李昂描寫之冷冽的筆調,幾乎成為對比,讀者正正能感受到林市的斷裂感。而對林市來說,她終於拿起刀朝陳江水身上砍下時,她正是在過渡(pass)而「成為」陳江水,成為一直以來在那個時代、敘事中持刀屠宰的男性角色。回到電影,此段落鏡頭特寫夏文汐的半身,並沒有拍到被砍殺的男性身體,也不特寫執刀的手部動作,只見噴灑在夏文汐身上的血斑隨著一次次落刀拔刀而範圍愈擴愈大。抽格放慢的處理,則讓我們同林市一樣,彷彿掉進了一個輪迴,一個恍惚若夢的狀態裡。林市的女性身體像被附身一般執行著男性角色、男性身體習慣的動作,而這樣的「慢」與不同角度具相當重複性的畫面,則正是那曖昧、過渡性的陰性狀態。

我想起《敢曝教母:美國的女性扮演者》(Mother Camp: Female Impersonators in America)一書中,埃斯特.紐頓(Esther Newton)如此寫:「變裝說:『我的「外部」表象是陰性的,但我的「內部」本質是陽性的。』與此同時,它也代表了相反的反轉:『我的「外部」表象是陽性的,但我的「內部」本質是陰性的。』」(註1)在李昂的敘事和夏文汐的銀幕形象中,陰性與陽性身體、動作的交織就是讀者/觀者的陰性視野敞開處。若說,1980年代初,戒嚴時期的臺灣社會,由《婦女新知》雜誌社等群體推動的性平倡議,關注著兩性如何在法律、基本權利上達到平等。那麼《殺夫》電影及小說,則在這些幽微的性/別角色、身體的置換與內外相交融,以及那從家屋內部的「傳統女性角色」過渡到執刀殺夫主動者位置的精神與潛意識狀態中,啟發觀者思考這兩性的身體、社會角色邊界,以及它們如何相抗衡之題。而來到2024年,臺灣社會處於後「#metoo狀態」,性/別運動以不同樣貌面世,看著酸六在台上以其身體之柔演繹林市從受暴後出逃後反擊的,介於夢與現實、流動在陰性與陽性間的狀態,則讓我們看見陰性擁抱陽性,反制、或與之交融的可能。
紐約與蘭嶼間的「溪流」通道:《鮮殺》
可以說,影像的陰性空間是一種曖昧的介質。同樣在「她的新電影」一檔展中另一單元「新電影外的她」聚焦「展映八〇、九〇年代在新電影歷史視野之外的女性創作者與作品」,這些創作者雖未直接參與推動彼時臺灣新電影運動,卻仍為當代電影產業注入一股非典的能量。旅法的臺裔美籍多媒體藝術家鄭淑麗首部劇情長片《鮮殺》即展現了影像成為一種陰性介質、通道的可能性。時隔30年,如今觀看本片依舊不過時,鄭淑麗透過轟炸性、快節奏的影像、媒體,堆疊出一則關於資本、消費主義社會的寓言。電影開場,我們看見剪影下的蘭嶼傳統拼板舟漂浮於落日的海上,接著,彷彿新聞畫面插播一樣,切接到一則藍底白字的廣告─「島嶼出售」(Island for Sale),以及出售洽詢的電話號碼,畫外音播送著廣告內容,下一顆鏡頭則來到紐約港,有人提著電視機走在街上,經過堆滿垃圾、二手雜物的貧民窟,快速的搖動鏡頭,即展現了這個區域人們背景混雜的狀態,不同族裔、膚色、階級的人們聚集,成堆的彩色電視與畫外音持續播送的廣告相呼應。接著,鄭淑麗巧妙地透過電視媒體的內容剪接回到蘭嶼,島上的人們身旁並置著播送西洋廣告的電視機,小男孩朝著被浪沖上岸的電視機丟石頭。

電視媒體,以及觀者所見的銀幕媒體成為一種介質,影像上連接起不同時空的敘事,敘事中則連接著東、西方場域;象徵著原始部落,以及消費主義的兩地。在步調極快的「紐約故事」中,蘭嶼島成為不斷被「接上」的遠方,以播送的新聞聲音作為音橋,影像上流動、空間感曖昧的海浪和海岸作為通道,紐約的事物漸漸飄洋過海來到蘭嶼。如同通訊一般,銀幕媒體將兩者接通。更有趣的是,這樣的「通」和介質,在鄭淑麗的佈局下,也成為其安放彼時所謂「邊緣」群體和身體的空間。片末字卡提及,「殺」(Kill)在荷蘭文中意為「溪流」(stream),可以說,《鮮殺》本身就是一條陰性的溪流,不同的邊緣身體漂流其上,女同志在此流通中做愛、原住民與無家者,美國各色人種與族裔之人在這些場域裡自由活動、相互交織。所有人一同透過不同銀幕、媒介,體驗和回應這個正進入消費、資本主義的社會。而在這過渡中,許多事物懸而未決,正如同那不斷被打斷的剪接斷點,卻又成為一種「流」地與他處、他者族群產生連結。鄭淑麗別具洞見的陰性目光意在打造既架空卻又貼近現實的時空,「她對電影空間的運用,與其說是在指涉特定地域,不如說是一種探索路徑的流動方式」(註2),是故她筆下角色的行動極為重要;空間與空間的轉介亦然,這樣的「介質」有著探索的開放性。
安藏在門縫間的陰性身體:《私角落》
「孽子們的天空:台灣同志電影選」選映了紀錄片《私角落》(2001),「Corner’s(角落)」是間男同志酒吧名,而「私」則是導演周美玲與劉芸后的拍攝視角。她們巧妙地將自己的感情放進了紀錄片中。「我要讓妳聽見,我因為想念妳,而自慰的聲音」,開首畫外音以法文道,畫面第一人稱視角拍著走進酒吧的步伐,「我」的存在如此鮮明。周美玲與劉芸后訪問多位酒吧中的同志,除了訪談,畫面亦溢入定格的赤裸、做愛的女性身體。酒吧場合具有某種「公眾」、群體的意義,然而「私」如何可能發生,即是《私角落》最有趣之處。作為一名女同志,在變裝發生著,性別身分游移、曖昧,陽性與陰性相交織、碰撞的場合裡,我與我的攝影機如何安身?

影片中強調了拍攝者介在門縫之間的位置,而我想《私角落》的詩意即存在這個曖昧、混沌、漂泊不定的位置。21世紀初,當同志遊行尚未集結,相關爭權運動、倡議只零星存在,正如《私角落》片末強調,同志群體在車水馬龍的臺北街頭仍感流浪、無鄉,周氏與劉氏的影像與日記體的畫外音記錄下了這種尚未完全顯身陽光下的「私」的狀態,那種依存在門縫角落才感到安全的處境。是故,《私角落》的陰性即在於:我們何以在縫隙中安身,在那些半公開的場域裡談論性、性/別身分,展演尚未合法的婚姻,尚是禁忌的性愛身體,在影像空間裡覓尋尚失落的鄉。

結語
今年跨性別遊行以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為起點與終點,十月底夜晚微涼的臺北,人們團聚。我想起《孽子》片中的公園場域,成為人們的庇護與「幽會」處,角色們時常以剪影的樣子出現在此。我眼前熱鬧的場景與電影中公園的陰鬱形成對比,當性別倡議成為群聚的運動,當那些曾經的剪影一個個在光與色彩斑斕的變裝、旗幟下被照亮,當「私」被打開而進入「公」,陰性與陽性在內內外外交織、相碰,「家」的場域便漸漸形成。影像中的陰性,原來在於介質、交融,與曖昧,這些是穿過、通過、過渡的必須。受暴的女性身體何以穿過恍惚的夢境狀態,而執舉男性身體長年掌控的刀;被排拒於社會進步「中心」外的邊緣角色,何以在快步調的敘事裡安身;而那些仍無家地生活在角落裡的人,又怎麼找到私我的位置?關於「她」、關於「孽子們」(曾)被視為「不完整」的身體,用影像作為陰性介質,讓我們重建一個中心。
註1 Newton, Esther. Role Models, Mother Camp: Female Impersonators in Americ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此處中文翻譯為《性/別惑亂:女性主義與身分顛覆》中引用段落之翻譯。可參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性/別惑亂:女性主義與身分顛覆》,臺北:時報出版,2023年。頁360。
註2 “Her use of cinematic space is less about a rooted territorial reference than a fluid way of exploring routes.” 可參Lawrence Chua, “Shu Lea Cheang by Lawrence Chua Shu Lea Cheang’s film Fresh Kill is non-stop motion, traveling between environmental and cyber space,” BOMB. Winter 1996 Issue, Jan, 1st, 1996.
本文原刊載於《今藝術&投資》2024年12月號387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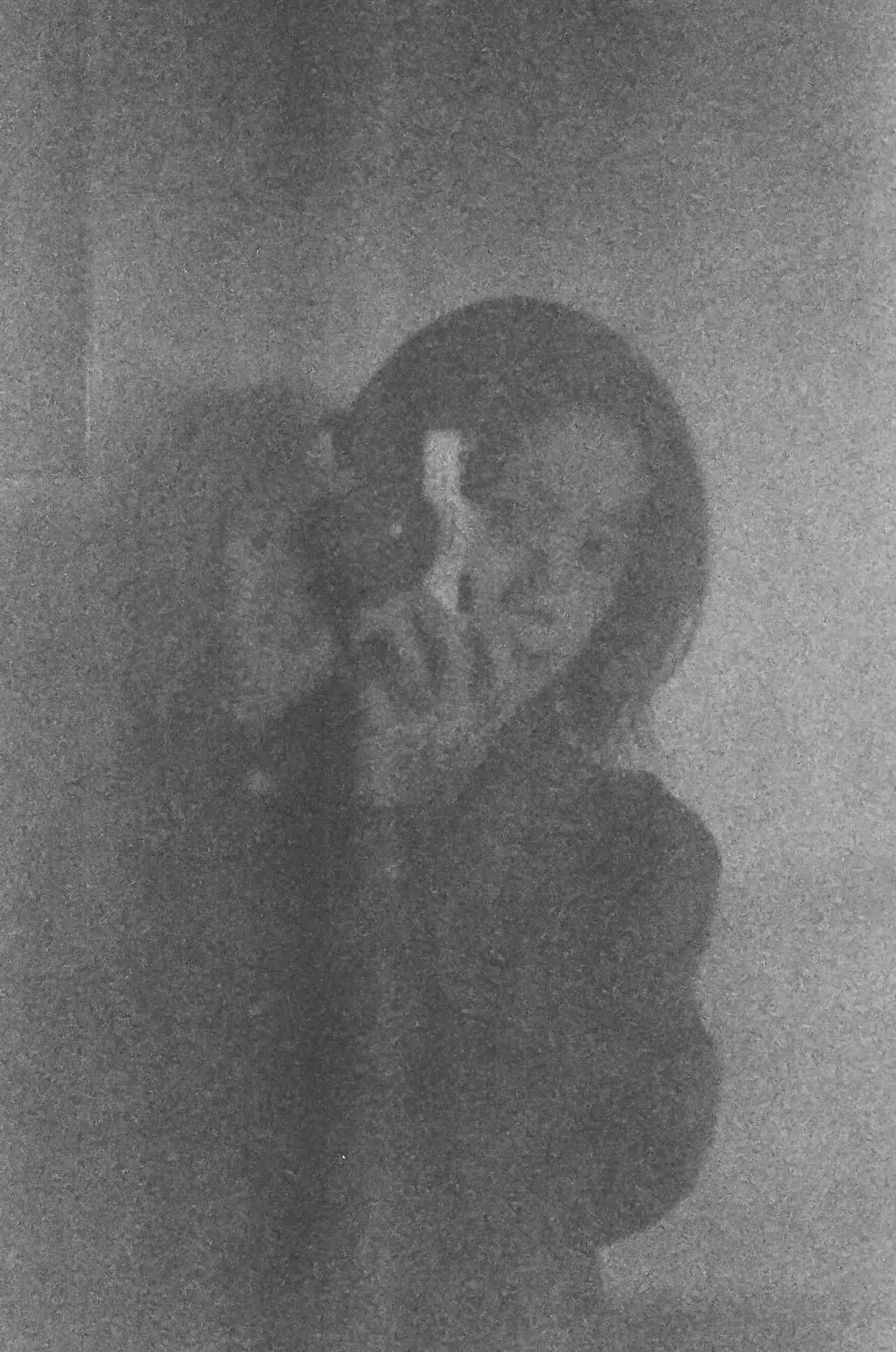 翁皓怡( 1篇 )追蹤作者
翁皓怡( 1篇 )追蹤作者臺大中、外文系畢,書寫電影與相關專訪,也從事影展工作。第八屆金馬亞洲電影觀察團成員,曾任酷兒影展影評人協會推薦獎評審,文章散見各藝文媒體與刊物。關注女性創作者,紀錄、實驗,與散文電影。Instagram:cathparadis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