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夏(2022),泰雅族藝術家林安琪(Ciwas Tahos)在紐西蘭的Artspace Aotearoa舉辦了她個人目前為止首次較完整性的個展「Finding Pathways to Temahahoi」(mgluw tuqiy na Temahahoi/找尋迭馬哈霍伊的路徑),相較於大部分身在台灣的原住民藝術家將其藝術生命的核心指向自己族群的所在(不論是精神意義上或地理意義上的——),林安琪所選擇的展覽場域、乃至於她的作品,幾乎帶有某種隱微悖向前述核心場址的意味,一種不全然朝向其「母土」的發展。
此一策略致使林安琪的跨地域性色彩稀釋了她的「本土」色彩,成了近年台灣原住民藝術場域中頗為特異的一位創作者。然而如若細觀她的創作路徑、乃至於此一路徑與台灣原住民藝術場域的關係,或可推知,她「看似」游刃於各種身分政治的跨地域性發展,實則徵示著、或起源於其背後頗為複雜的「雙重匱乏」處境;林安琪的創作歷程,也幾乎可以作為對此狀態的綿長回應,而迸發出的某種無法輕言收束的、自成一格的創作力量。
「都」與「酷」的雙重匱乏
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主要延續著1980年代、解嚴以後「本土性」與「主體性」的政治風潮,並承接著彼時社會運動的思想脈絡,在1990年代逐步發展起來。是以在過往的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中,它通常與某種建構中的民族思想和族群情懷相關,並高度關聯著族群內部既有的文化內容與結構。
在這樣的語境裡,某些殖民時期被抹除、被賤斥的族群經驗的確透過創作者的積極復返而得以銜接、拼湊,然而在這個重新形構族群主體的過程中,也隨著各種權力階序的組合運作,創造了某種「正典」的身分敘事,排除了某些難以被闡釋的重重複影。爾後這些複影,包括出生在1980-1990年代、因父母輩的離鄉背井而與自己的原鄉場域脫鉤的「都市原住民」,以及在近代的二元性別系統中難以被歸類的「酷兒原住民」。
在藝術創作的向度裡,他們一則難以再如過去的藝術家、積極而正當的復返於其母體文化場域並進入某些技藝與記憶的典範承傳,二則甚有可能需要在既有的結構關係裡重新創造自己的身分正當性。出生於1980年代後期、並自我認同為「酷兒」的林安琪,即承接了此造被「排除」的兩種身分敘事,迎來了兩造身分中雙重的匱乏處境。
在林安琪接觸藝術創作以前,她國中就被送離台灣,到加拿大生活了13年。事實上,林安琪對於自己的原住民血緣一直處於懵懂狀態,直到長大後,在一次返台搬家的過程中,發現一條外婆留下的殘碎項鍊,透過這唯一的物質線索,才開始挖掘自己的身世之謎。但是母親對這一條項鍊也所知不多,只能依稀回顧項鍊源自於外婆的泰雅家族。
母親的態度未明,其中因素,不只是因為此造族群身分所曾共同承受的壓迫記憶,在林安琪多年後的追索,才知道母親乃至於自己所承繼的血緣敘事,還在於外婆身為一名女性,當年是一個被送走的、身分難明的孤女。也就是說,這一條由外婆而至母親、再從母親至安琪的母系血緣系譜,不僅僅徵示著「泰雅」此一意符在不同世代中的情懷變異,還闡連著「女性」、「離散」與「酷兒」——一組串接了三代完全不同的女性生命的複雜語境,成了某種極非典型的、難以輕易銜接的身分文本。
林安琪前期的作品,幾乎反映著這樣的困惑與徬徨。她帶著項鍊與諸多謎團回到加拿大,開始創作如《紋面》(2014)系列的作品。此一時期,林安琪的作品充斥著某種疏離與焦慮,然而這樣的焦慮,又與身在台灣本地的原住民藝術家、盧梅芬所謂自拉黑子.達立夫(Rahic Talif)以降的認同焦慮與美學焦慮(註1)完全不同。
在林安琪的身上,某種「原住民」的認同路徑幾乎尚無線索,她的性別難題使她遠離家鄉、族群身分宛如一團迷霧,在《紋面》裡,她用膠帶把自己的嘴封死、再用簽字筆在膠帶上畫出歪斜紋路,她的困惑與徬徨,不只預示了她終將難以走入前輩論者的界分之中,甚而只能由自己「撕開膠帶」、開口回應這個並不普遍的生命處境。

神話轉生術:航行酷兒烏托邦
2017年,林安琪回到台灣,開始意圖尋找更多線索。此時期的她速寫了台灣當代都市原住民的集體徬徨,在《獨木舟》(2016)裡,她找了八位與自己一樣在大城市生活的原住民女性,用掃把仿擬「划槳」行為,在一個潔淨的封閉空間裡,掃出陣陣虛擬的海浪聲。從膠帶上的紋面,到白盒子裡的海洋,林安琪作品中的原住民符號是斷裂的,然而她雖看似無以複寫過去的原住民認同者所建立起來的某種「復返」範式,現實生活中,其實保持著高度的敏感與積極,在重新拼湊自己的身分之謎。
2019年,她透過幾年的尋訪,終於從早已斷聯的遠親口中,找到外婆的名字與部落。這期間,林安琪亦如台灣這一代的許多原住民青年,努力挖掘家族史、學族語,反覆歸鄉訪查,然而這一切,卻在她的作品裡被複調呈現,成了一種積極意志與抵抗意志下,詭異的、悖論的「反認同」、「反系譜」。
北美洲的原民酷兒研究中早已指出,「原民酷兒」與「民族主義」之間,存在著難以辨明的衝突與合作關係(註2)。對「原住民」-「酷兒」認同者而言,他們一則接受了族群身分的召喚,一則對族群內部的權力結構保持著抵抗與質疑;一則在無論承傳自母系或父系血統的生殖主義語境中尋根覓系,一則在二元性別系統之外的酷兒身體裡左右迎擊。
之於林安琪,她依然加入拓樸學的行列裡,拼湊祖先的遷居途徑;依然步入山林,尋訪歷史的痕跡。然而她無法只是將之檔案化的呈現出來、迎頭趕上人類學式的民族誌踏查,在原住民酷兒與民族主義的角力中,她終將掙脫寫實意義下的歷史想像,朝向一個近似於José Esteban Muñoz所謂「酷兒烏托邦記憶」(queer utopian memory)的創建工程(註3),一個建構在未明的過去、與未到的未來之間,提供著酷兒想像與批判視野的烏托邦世界。

2020年,林安琪的《她可能來至__社》,為此造烏托邦敘事拉開序曲。創作過程中,她一邊復訪外婆的舊居地「Plngawan」、連結失散的親緣,一邊又在這種匱乏的情感結構中,為自己「創造」了一個「母土」。而這個母土文本的原型,不在任何一個現實地理中的場址,而是一個叫作「迭馬哈霍伊」(Temahahoi)的神話之地、一個除了她所屬的泰雅族外,許多台灣原住民族乃至於世界民族都有的「女人部落」神話。
這個神話雖然各地版本皆有殊異,在台灣原住民的版本裡,大部分又與某種「非人」想像有關,在晚期流傳的版本中,並常常可見某種「人族」與「非人族群」的對立、以及「我族女性」與「他族男性」的對立關係(註4)。對於這個只有單一性別、並有高度「非人」指涉的神話故事,過去的人類學家無以輕解其背後的象徵意義,但在林安琪的眼中,它就是某種酷兒情感/情慾模式的遠古原型。
在《她可能來至__社》中,林安琪透過數位科技,在網路世界創造了一個雲端故鄉。觀者必須掃描短網址進入,並透過屏幕,一訪這個虛擬的母土。然而在這個虛擬母土中,林安琪卻串起了她與外婆的連結。「__社」的地形佈局,大量參照著Plngawan的地理模型,起伏的土地上再豎立著一張看板:「尋人啟事:尋找Ciwas」,Ciwas是她外婆的名字、一個當年被送離村落的泰雅女孩;林安琪也把自己的族名取做Ciwas,一個數十年後再被送離家鄉的泰雅女同志。

在林安琪所創造的「__社」中,古典神話被她轉化為一則高度自我文本化的「私神話」,「迭馬哈霍伊」的單性繁殖寓言,一則隱喻了她承繼自兩代女性的母系血緣,一則映照出她無論在泰雅身分或性別身分的認同場域中,皆一反文化常態的、全然空缺的男性角色。
於此,「__社」當然不是對於族群歷史的寫實補遺,而是試圖打造出一個安頓了此造酷兒認同及批判視野的時空。這個虛擬的、神話的母土,隱微的指控了當代新歷史主義下踏查行動與復返意志裡潛在的異性戀精神結構,此間酷兒的認同取徑,亦拓闢了過往人類學家無以闡及的神話意義,「迭馬哈霍伊」從一則謎樣的神話文本,轉生成為原民酷兒的精神故鄉。
延伸閱讀|卡拉永遠OK:客廳、酷兒、家族系譜

民族主義轉向:以「酷」之名
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的30年發展中,最早透過一系列藝術創作展現出某種強烈的多元性別政治意圖的創作者,或以太魯閣族的東冬.侯溫(Dondon Houmwm)最為人知。然而東冬近年的發展,從個人式的藝術創作,轉向以「銅門部落」為主要據點而擴展出來的社群性、集體性的藝術行動,某種哲學體系包括性別觀點的重新建構,正在這種隸屬於特定族群的文化知識場域中蓄勢待發。
然而在林安琪身上,她所實踐出來的藝術力量卻顯然與東冬朝向不太相同的方向。相較於面朝一個實際意義上的「母土」、原鄉部落,林安琪與「Plngawan」之間的斷裂,致使她必須透過「__社」來自我填充這一段記憶與情感的空缺。然而當「__社」的敘事空間透過她的自我文本化、古典神話與酷兒寓言的交織而逐步擴展開來,林安琪的「無社群」性也開始出現變化。在《她可能來至__社》之後,林安琪透過接續的一系列作品,著手尋覓其他的原民酷兒女性。藉由她們的現身,林安琪開始創造她想像中的「__社」的(偽)歷史敘事、風景與圖像,並出現了一種非以特定「族群」之名、而以「性別」之名的、跨族——「酷族」社群,的集結傾向。
也就是說,如若前述「酷兒烏托邦」的建置將有其集體意義上的發展,林安琪的創作中開始出現的「跨族結盟」,或許將拓展出此造「烏托邦」意義的更廣格局。其甚有可能拓及的,除卻她個人的生命史,是否還徵示出此一世代原民酷兒的情感叢像?如若如此,「__社」的「__」喻說,即不再只是無名、斷裂與空白之域,而是某種民族主義的界線溶蝕、以「酷」為名的群像顯影。
作為原住民認同世代的其中一位創作者,林安琪略顯特異的創作策略,不只因為她過去所受的藝術訓練,實則還有一頗為複雜的世代背景、及此背景下異質的認同經驗。這些經驗致使她與某種「原真性」想像下的原民意象頗有差距,然而這種差距,是否正徵示著過往民族主義及二元性別的認同結構中、不自覺被重新寫就的霸權敘事?在原住民當代藝術30年的發展中,有過幾次意義重大的轉折時刻。
於我而言,自2010年代以後,東冬、安琪與其間的幾位藝術家之於原民性與酷兒性的交織辯證,或許也將成為此時當刻,一個正在發生中的、極其重要的轉折時刻。

註釋
註1 盧梅芬,《臺灣原住民族藝術發展脈絡研究:以木雕為例(1985至2010)》,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2012,頁340-346。
註2 Qwo-Li Driskill, Asegi Stories: Cherokee Queer and Two-Spirit Memory,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16.
註3 José Esteban Muñoz, Cruising Utopia: Te Ten and Tere of Queer Futuri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9.
註4 關於台灣原住民族與世界各地女人社之比較研究,參見李福清(B.Riftin),〈從古希臘到台灣-女人部落神話比較研究〉,《神話與鬼話-台灣原住民神話故事比較研究(增訂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責任編輯|陳思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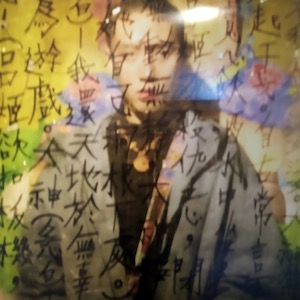 呂瑋倫(Wei-Lun Lu)( 8篇 )追蹤作者
呂瑋倫(Wei-Lun Lu)( 8篇 )追蹤作者策展人、藝評人,關注原住民藝術、後殖民與性別理論研究。近年策劃包括「后古事紀:當代原住民變裝表演叢像」、「情山色海:酷兒.原民.祕密史」、「母神的備忘錄:武玉玲個展」等展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