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屆沙迦雙年展(Sharjah Biennial 16)「to carry」於本月正式開幕,這一遠在阿拉伯世界的藝術盛會自創辦起至今32年,終於與台灣的藝術世界有進一步的關聯,委實是一件有趣的事。
此言並非意指過去的沙迦雙年展沒有出現過台灣國籍的藝術家,然而本屆受邀參展的武玉玲(Aluaiy Kaumakan)與林安琪(Ciwas Tahos),無非是在近年世界性的思潮中、連結著某種深刻本土性而被大家所熟知的「原住民」藝術家,也就是說,某程度上,她們都是帶有非常鮮明的地域特質的。沙迦雙年展亦如是,作為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最有名的「文化」國度,沙迦藝術基金會一直積極建立著中東世界的藝術主體性,並逐步與歐洲國家的雙年展做出差別。
不過,翻開近代歷史,在台灣原住民與阿拉伯世界之間,幾乎沒有什麼太直接的關係。當然,即便是強調地域主體性的雙年展也不必然要與參展的作品有絕對的文化關聯,過去的沙迦雙年展也並非沒有出現過全球原民性的作品,不過如果這裡真的有關聯,那可能會是什麼呢?為什麼在沙迦雙年展的32年後,一次邀請兩位台灣「原住民」「女性」藝術家?除了樣板式的、成功的文化外交成績單,這於台灣的藝術世界、事實上又有什麼意義?
以「女性」之名:過時與未竟
曾幾何時,以「女性」(甚至是「性別」)作為藝術或文化行動的策略或主題,成了某種類型框架甚而被視為有點過時的語境。當代藝術世界的主流意識向來貼在紅火思潮的屁股後面,女性主義在轟轟烈烈的1990-2000年代後,終究漸漸被歸回特定族群的生命政治之中,不再被作為一種「新鮮」的方法。然而本屆的沙迦雙年展,一個不容忽視的強烈意圖是,它就是要重新面向這個「半古典」的「女性」方法論,即便女性主義(或說過度帶有某種女性主義意味的修辭或語境)被分明全都是女性的五位策展人在其論述中淡化或不提,它依然像一叢複調的回音,懸繞在沙迦城市各處的展場之際。(註1)
。這件作品的靈感來自於一個在父權社會的傳說敘事中被認知為可怕女巫的Calon-Arang。攝影:呂瑋倫.jpeg)
此言當然並不意指本屆沙迦雙年展只圍繞在「性別」框架下,事實上,「to carry」在五位策展人的策劃下,共邀請136組藝術家、超過80個委託創作、散落於沙迦城市13個地點之中,其思想、論述與展演規模之龐大,絕非一言能蔽之。此文意欲重提「女性」方法的重要性,一來是這一在某些地方已被認為不夠「新潮」的主題與策略,在本屆沙迦雙年展中依然滾動出特殊的意義,二來它也是武玉玲與林安琪(台灣原住民女性)的藝術實踐與中東世界闡連的關鍵之一。

以武玉玲為例,她的藝術生命一直與莫拉克風災後召集被迫遷村的部落婦女們一起創作、面對集體創傷,有很大的關係。在本屆雙年展裡,這種集結於近代殖民帝國之外的、不同地域的女性藝術社群,是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大量的織品、纖維藝術與女性團體的勞動創作,廣泛分散在不同場域之中,其在技術上與視覺上有時甚而逼近過度相似的藝術展現(就這點而言,武玉玲的作品在其中依然有極大的辨識度),卻也拼組出此際特定性別在某種藝術方法上磅礴的共時性。

》(Gori-Leso-Leso-Daily-Working-Life-2024)。Güneş-Terkol擅長透過工作坊的模式與世界各地的女性團體合作,此作邀請印尼.jpeg)
,2020-2024。攝影:呂瑋倫.jpeg)
除了這種「結盟」式的女性群像,也有一些作品聚焦在殖民歷史夾縫中的形單女人。她身影謎樣,難以歸類,隱喻著各種治理術下的未明之事。對我而言,林安琪則照見著這種祕密與禁忌,她的參展作品雖非近年受到諸多關注、帶有原民酷兒意識的「女人社」系列作,但暗藏其中的肉體意符,依然騷動著以當代伊斯蘭信仰為主的文化秩序場域,讓人想起它曾極致豐饒的同性愛欲史,以及在男女處境的差異下,女性社群消失似的、祕密般的酷異史前史。(註2)
1944年離奇車禍身亡的作品《Clear-Night》(2025)。這場死亡事件實則牽涉著英國與法國的「秘密戰爭」,其中亦.jpeg)
流域舞蹈、歌謠與傳說的作品《Boundaries-of-the-Dreaming-Body-Tajliba》,2025。攝影:呂瑋.jpeg)
,一個性別模糊的身體,與一圈暗喻女器的陶瓷。攝影:呂瑋倫.jpeg)
事實上,回到台灣原住民藝術的脈絡之中,武玉玲與林安琪亦標示著兩個端點的原民情境。武玉玲的藝術實踐高度回應著緊密的族群關係與親緣連結,她藝術生命的轉捩點甚至在於風災之後、返身走回某種古典的結構之中;林安琪則完全體現著1980-90年代出生的「混血」世代,斷裂的族群記憶、頻繁的移動經驗,迷離的家族離散史與積極的酷兒認同。如果台灣的原住民當代藝術有一種差異情境的光譜,這兩人,正好各自標誌出一種極端。我不知她們是在何種情境與考量下被五位策展人之一的Alia Swastika選入雙年展中,若非誤打誤撞,策展人確實做出了非常精準的選擇。
跨地女性與文化協商
然而伊斯蘭中東地區的文化特殊性,依然牽動著各種圍繞在性別與跨地域文化上的現實問題,這也是沙迦雙年展的極致特別之處。以林安琪為例,她原本受邀參展的作品因有裸身女體,在兩造協調下只能更換展件,「穿上衣服」重製一件十年前的舊作《海岸》(To the Shore)。有趣的是,在這個重製計畫裡,林安琪操演了一個性別模糊的身體,不裸露任何部位,彷若不屬於任何性別。這種順應「不裸露」而達致的性別未明,與當地的性別與衣著文化出現了一種相抵的身體政治。
把身體「收起來」的現象亦不只發生在林安琪身上,開幕當天,這是一部分女性藝術家共同的話題之一。她們將身體意象轉化成符號、圖紋,在地的文化規訓致使跨地域的當代藝術現場成了一個饒富神話學意味的女體迷宮。在其中一個展場Calligraphy Museum裡,印尼藝術家Citra Sasmita的作品將大廳佈置成三座牢籠,聖杯、蛇紋和女形神獸護守著一則失落的女王故事;事實上,她過往的作品皆聚焦於峇里島神話與文學中的父權意識結構,在過去的展覽中,裸身的女體亦是她作品裡常見的意象,然而在沙迦雙年展的現場,她們全部以某種賽博格體現身。
沙迦雙年展中大量如是神話般的女體,幾乎創造出一種與西方藝術世界完全不同的、特屬於此造政治脈絡下的陰性圖景。即便在看似與穆斯林性別文化較不相衝擊的排灣族脈絡美學,武玉玲展場裡一朵悼念母性器官的纏繞花苞,也得任其不言而喻。

中,與神聖犀鳥合為一體的女人。攝影:呂瑋倫.jpeg)

這種在地文化與跨地域當代藝術的扞格問題,其實一直圍繞在沙迦雙年展的場域之中。只是本屆從策展人到參展藝術家裡強烈的女性主體性、大量現身的隱伏在近代帝國之外的女性身影,或甚至是更幽微的酷兒喻說,都更放大了這種「文化」與「性別」的扞格。相較於一些西方世界的「現代性」之眼或曾藉此影射對阿聯酋政體及社會文化的批評,(註3)我傾向認為這些藝術家的跨地域藝術實踐,其實在強勢的國家制度與律法框架下,透過各種抒情、隱喻、參照與揭示,協商出一個在體制的陽剛與專制裡的複調時空。
我私自浪漫以為,這也是在堅實的父權皇室傳統中長大的沙迦公主、同時也是沙迦藝術基金會總監與雙年展重要角色的霍爾.阿爾.凱西米(Hoor Al Qasimi),藉眾女之口,為她古老而尊貴的血統所拓闢的出逃記。
,柔軟齊整的織布與織具被展示在一座荒廢畸零的石造建築裡。攝影:呂瑋倫.jpeg)

。此作陰柔化的體育文化,令人玩味不已。攝影:呂瑋倫.jpeg)
原民「性」的本土稀缺與跨國趨勢
如果台灣作為此一藝術事件的另一個論述座標,武玉玲與林安琪在阿拉伯世界的出展、或甚至是說,此二人近年在國際展覽系統中的頻繁上線,(註4)或許也有令人反思的意義。正如前述,此二人在其藝術實踐上的方法與脈絡,皆高度展現出某種原民性與性別關係;武玉玲緊密的母系承傳、婦女社群系統,林安琪離散的母系族史、跨族酷兒結盟,正高度拓延著兩種當代原民的性別敘事。當她們開始受到廣闊矚目而漸次輸出小島,也代表「族群」與「性別」的闡連政治,應能滾動出龐大的、跨地域性的藝術能量。
然而我亦曾指出,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自1990年代發軔以來,在原住民族群研究場域或藝術場域進行性別研究,就一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註5)它曾極度小眾,在過去各種由男性主導的意識形態戰場中被長期忽略,至今又被歸類在某些特定主義的框架類型之中。作為此際小眾又類型化的研究者,在我對武玉玲、林安琪以及台灣目前幾位原住民藝術家的觀察中,我依舊認為台灣的文化與藝術研究至今忽視此一發展的重要性。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的世界性,在此是以「性別」為軸心輻射出去的。
回到沙迦雙年展本身,這一持續擴展的、包山包海的「南方」論述版圖,在這一屆有了另一個迴繞著「女性」主體的定錨,它之特殊與重要,亦在於其跨地域的、互相捲動與參照的後殖民女性視角,正豐碩著伊斯蘭世界的文化景象,亦迫使世界重新思考其性別歷史與文化上的複雜性與可能性。本文聚焦於斯,亦是在龐雜如迷宮、廣散至沙漠的展覽現場失魂遊走時依然不可能忽視的女性身影處處,我想起我遇到的一個敘利亞男孩,阿聯酋好多這種從中東不同國家跑去賺錢的移民,他的家在戰爭中炸毀,爸爸病危,弟弟在渡海逃亡歐洲時死去,剩下母親一個人留在敘利亞。
為什麼她要留在敘利亞呢?我或許有點明白迦雙年展為何終至定錨於此,即便它的政體國情總與此造女性語境有一種唐突之感、即便在世界知識生產的光速更新下有一種古典氣息,我依然感覺到無盡的陰性力量與問題叢結,穿梭在現場各種「女性」的局部之間。藝術的轉譯即便達致緩衝,有時依然令人屏息。
在印尼曼加萊(Manggarai)駐村期間與當地女織工合作的作品《從這裡,到那裡》(From-Here-to-There-2024)。攝影:呂瑋倫-1.jpeg)
註1 本屆沙迦雙年展史無前例的邀請五位女性策展人共同策劃,分別為Natasha Ginwala、Amal Khalaf、Zeynep Öz、Alia Swastika、Megan Tamati-Quennell。
註2 16-18世紀的伊斯蘭文化世界其實有豐饒的同性愛欲文化,不過目前的研究多以擁有較高社會階級與知識力量的男性為主,因他們留下文字。我曾以為這段歷史在今日的伊斯蘭世界是禁忌,直至這次在沙迦市中心的伊斯蘭文明博物館中看到他們直白寫出自己過往的情詩描繪對象通常是女性以及年輕男子。關於穆斯林同性愛欲史及其「美少年崇拜」,參見Khaled El-Rouayheb, Before Homosexuality in the Arab-Islamic World, 1500-1800,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 2009.
註3 Max Lunn, New vision at the Sharjah Biennial, “Perspective Media,” 2023.
註4 武玉玲自2020年開始陸續受邀參加日本橫濱三年展、台北雙年展、澳洲亞太三年展、雪梨雙年展,今年除沙迦雙年展外還有赫爾辛基雙年展邀約;林安琪於沙迦雙年展期間還有夏威夷三年展、南非泰斯倫博斯三年展(Stellenbosch Triennale)三展同時進行。
註5 呂瑋倫,〈山海酷族: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中的酷兒路徑〉,《文化研究季刊》188期,20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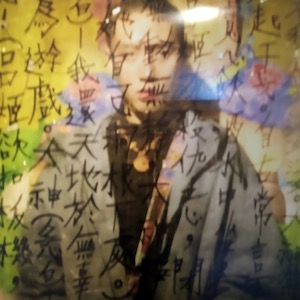 呂瑋倫(Wei-Lun Lu)( 8篇 )追蹤作者
呂瑋倫(Wei-Lun Lu)( 8篇 )追蹤作者策展人、藝評人,關注原住民藝術、後殖民與性別理論研究。近年策劃包括「后古事紀:當代原住民變裝表演叢像」、「情山色海:酷兒.原民.祕密史」、「母神的備忘錄:武玉玲個展」等展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