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迴返計畫」是同時身兼教育者與拍攝者的陳敬寶,透過學習單的意見回饋收集學生與家長對於校園生活、兒時記憶的回想,然後引導幾位願意配合的學童利用課餘時間搬演而成。其中,最首要的問題便是如何理解這些孩童的生活形貌。因為孩童世界的再現,經常有過於扁平又片面的弊病,往往不是為了滿足成人凝視下所強加的純真概念,就是區從於一種懷舊式的刻板童年想像。而華人社會慣常的幼體化對待,更是經常將孩童貶抑為不具有主體性的人,這點誠如郭力昕的觀察:「華人、或深受儒家觀念滲透的台日中韓等社會,普遍不習慣或不願意賦予孩子以完整的人格,以至於兒童在成長過程,總受苦於傳統儒家社會裡成人威權性格的心理傷害。」(註1)而這種儒家思想教條的運作場域,除了家庭之外,最重要的便是學校教育;校園生活正是一個人逐步形塑其價值觀、品味喜好、行為模式,乃至於生命態度的規訓場域。因此,「迴返計畫」除了召喚人們有所感觸或早已遺忘的記憶場景,其實也指向成長過程中最根本的生命政治力量。校園本就是一個規訓空間,而孩童本來就在其中經受著生命政治層次的深刻模塑,因此陳敬寶將任教學生轉為攝影題材所觸及的倫理界線,更顯得必須小心應對和處理。因為在搬演校園生活的邀請背後,仍無可避免地隱含一定程度的師生權力關係,倘若攝影家採取威權式的編導掌控,僅僅是將孩童視為可以任意擺布的被動人偶,那麼編導式攝影的操作就會是對孩童主體性的再次貶抑與壓制。

陳敬寶│老松計畫:體操比賽 Inkjet print、文件 102cmx122.5cm、30cmx21cm 2009
這點正是「迴返計畫」表面上看似平淡、單純,實則艱難無比的挑戰:陳敬寶一方面必須避免其攝影只是從成人眼光出發對校園生活與童年往事的刻板模塑;他必須保有對拍攝對象生命經驗的真切彙整與深描。另一方面,他也必須謹慎處理創作者與拍攝對象之間的關係,避免受他邀請而來的孩童淪為再現校園生活的布景道具,甚至使影像所打開的實踐場域成為二次規訓的教條化空間。可慶的是,「迴返計畫」巧妙地穿越了上述的困難障礙,在攝影家特意並置之靜照與學習單的來回閱讀過程中,我們毫無疑問仍感受到孩童們飽滿的主體性。以至於,這個從台灣出發並逐步擴及日本、韓國及中國的攝影計畫,為我們提供一個與各地學童之生命記憶相關,同時又能延伸省思亞洲四國教育制度或政治體制之異同的宏觀視覺文本,深具層次豐富的可讀性。

陳敬寶│黃金町計畫:夜觀星象 Inkjet print、文件
102cmx122.5cm、 30cmx21cm 2010
102cmx122.5cm、 30cmx21cm 2010
深度參與的攝影實踐空間
但具體而言,「迴返計畫」究竟做到了什麼,以至於能跨越前述的拍攝倫理難題?我認為,關鍵是其所敞開的特殊對話空間。初次閱讀「迴返計畫」的觀者,可能會對如此平實無華的畫面究竟有何特出之處感到困惑—陳敬寶幾乎不做任何後製處理的作法,在畫面呈現上既不追求奇詭的構圖或殊異的觀看視角,也不汲汲於任何戲劇性場景或炫麗光影變化的捕捉—這些攝影靜照背後雖然充滿著故事,卻似乎少了那麼一點人們習以為常的影像魅惑力。在這個影像奇觀被快速生產,同時又快速被遺忘的年代裡,「迴返計畫」毫無疑問是反其道而行的一套攝影作品。這是因為「迴返計畫」裡著力最深的部分,其實並不是攝影集或展覽空間中一張又一張可見的攝影靜照。
這並不是說,陳敬寶完全忽視攝影媒材最基本的美學追求,事實上他對畫面構圖、光影布置、場景調度,乃至於書頁印刷品質等細節是極其講究的。只是他的攝影美學從不停留在單純的觀看層次。倘若攝影家有意追求視覺表象上的感性張力,早從他過去的作品《片刻濃裝:檳榔西施攝影集》便可盡情發揮。但是我們看到攝影家從未這麼做,即使面對檳榔西施這樣的拍攝題材,他也沒有選擇任何煽動性、挑逗性的呈現方式,反倒是給予我們一種冷靜、端正、毫無任何偏見或修飾的肖像式凝視,極其尊重拍攝對象如何自我呈現的意願。「迴返計畫」雖然採取操作空間更大的編導式攝影,卻依然維持這種謹慎呈顯拍攝對象之主體性的攝影姿態。

陳敬寶│老松計畫:打掃環境 Inkjet print、文件
102cmx122.5cm、30cmx21cm 2009
102cmx122.5cm、30cmx21cm 2009
更重要的是,相較於「景框之內」可見、可感的視覺經營,陳敬寶在「迴返計畫」裡的努力更多是處於「景框之外」的。意即,有更多拍照之前與孩童們的溝通引導、意見交換及遊戲激盪,這些頻繁互動全然是不可見的。換言之,透過重新演繹校園生活情境的遊戲性邀約,「迴返計畫」打開的是一個雙方皆能深度參與,卻沒有任何壓力的攝影實踐空間。攝影家並沒有為了追求符合成人眼光及消費慾望的赤裸記憶,或者為了刻意挑起那些與責罰相關之規訓場景的戲劇性張力,而犧牲參與學童們的自主意願,甚至強迫他們直面那些屬於殘酷、幽暗一面的創傷經驗,以換取影像貼近現實的價值。扼要地說,「迴返計畫」裡的影像依舊維持它們做為一種「演示」,與現實之間保持著微妙的距離;它們主要是做為一種通往記憶(無論痛苦或愉悅)的「過道」(passage)、一種激發人們腦中影像的必要路標,而不是單純現實再現的終局(end)。
上述這點也提醒我們,「迴返計畫」終究必須被視為一部基於陳敬寶個人機緣與攝影之思的作品(因為幾次駐村或姊妹校交流機會而促成該計畫的跨國機緣),而不是某種大規模的社會文化考察或田野調查的直接紀錄。我們固然會因為這些重演的校園生活景致而聯想到各種或宏觀或微觀的文化政治議題,或者因為攝影家擴及亞洲四國的足跡而構築出一個具地緣政治視野的問題意識平台,但「迴返計畫」終究不能直接視為我們據以評論不同國家教育制度、政治體制、意識型態再生產,乃至於思想規訓力量的視覺性證據。要言之,「迴返計畫」無論在實體空間展示還是攝影集頁面編排上皆力求影像與文件的交互參照式閱讀,這點特質確實與許多人文學科的知識形式相當契合,極具思想的啟發性。但到此為止,攝影家已善盡打開議題與話語空間的美學責任。至於作品發表之後,能否促進更為縝密且符合嚴謹學術規範的研究活動,恐怕便是諸多文化評論者、研究者們的責任了。

陳敬寶│鄧公計畫:被罵 Inkjet print 102cmx122.5cm 2003
從現實影像到潛在影像
除了激發社會文化層面的議題思考之外,「迴返計畫」還有什麼樣的重要意義呢?我認為,其價值在於它強而有力地指向影像的「虛」與「實」兩端。「迴返計畫」裡的「現實影像」(actual image),指的自然是攝影家徹底發揮其才情,與參與學童們共同合力完成的一張張攝影靜照,這些都是人們可以相互評比、討論的感性呈現。但另一方面,「迴返計畫」卻又非常能夠觸動每位有類似經驗的觀眾,進而提取、召喚其腦海中的記憶影像;這些影像則是不可見的、人們難以相互討論的「潛在影像」(virtual image)。後面這種影像,我們又可稱之為「無機具影像」,因為它們不是經由尋常影像機具的光學機制所生產,而是直接在我們大腦中生成,同時也直接在腦海中播映的影像。
「迴返計畫」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於它沒有像一般的攝影實踐那樣僅止於現實影像層次的美學經營和追求,因為陳敬寶更在乎如何從可見、可感的現實影像出發,通達屬於記憶、想像,乃至於生命史範疇的潛在影像層次。據此,「迴返計畫」的意義更接近一種記憶的「觸媒」、一種無機具影像的啟動器,以通往每一個人心中各自不同,卻未必存在於現實中的生命史影像。在攝影集的開頭,陳敬寶特地援引法國作家莒哈絲(Marguerite Duras)在小說《情人》中的一段話。後者在小說裡時常一而再,再而三地緬懷她15歲時初戀的中國男人,言語間,充滿了當時沒能來得及為這段戀情留下任何一張照片的無限感慨。換言之,相較於人們有所準備並且適時拍下的影像,其實更多的是那些來不及拍的影像、不可能拍的影像,或者被人們遺忘/失落的影像—這些多半只能在記憶中迴盪的無機具影像,才是「迴返計畫」真正關切的核心主旨。由此觀之,與其說陳敬寶找到一種介乎真實與虛構之間,讓記憶變得可見的再現形式,不如說他創造了一種以攝影實踐為中心的溝通介面,讓每一個人都能藉由這些已具現化的感性平面,迴返各自心心念念或早已忘懷的過往時光。

陳敬寶│楓涇計畫:鼓號隊 Inkjet print、文件
102cmx122.5cm、30cmx21cm 2012
102cmx122.5cm、30cmx21cm 2012
雖然乍聽之下,一部無機具影像的歷史相當唯心而難以討論,但我認為「迴返計畫」的價值恰恰在於它巧妙地找到一種觸動人心、且具有相當參與性的感性形式。因為並不是所有攝影家都有心思或能耐超越視覺表象層次來思考影像生產的深層意義。在過去,張照堂也曾透過許多文字風格特異的攝影札記,來勾勒他所謂的「心有戚戚卻又無法捕捉的影像」。他曾有一篇名為〈非影像筆記〉的文章,裡頭蒐羅各種工作之餘的奇思狂想;這些並非出於文學性考量,而主要是以攝影之思為導向所書的詭譎場景,不僅讀來充滿歷歷在目的影像感,更是理解其攝影美學的重要線索。(註2)〈非影像筆記〉給予我的重要啟示是:我們有必要更宏觀地檢視攝影家所有的創作產物,如張照堂的攝影美學便存在一個由影像與文字相互補述的特異空間,需要以複合式的閱讀策略去貼近。「迴返計畫」也是如此,它也存在一個由影像、手繪圖像與書寫文字相互纏繞的複雜閱讀空間;而陳敬寶的攝影實踐,很像是在記憶的訊息洪流之中創造各個節點,並提醒我們那些沒能在現實世界中顯影的無機具影像,唯有透過這種方式才得以迴返人世。
待書寫的無機具影像史
至於無機具影像的書寫問題,陳界仁曾有一個關於台灣電影史起源的討論頗具啟發性。他指出,日治時期戲院裡設置的台籍辯士,經常會透過各種當時台灣民眾才懂得的俚語、暗語,去刻意曲解並扭轉原本殖民者意欲教化被殖民者的電影影像。因此辯士們的「錯譯」,會讓每一位觀眾的腦海都重構出截然不同的影像內容。(註3)正因為只有殖民者才掌握了象徵話語權的影像機具和播映科技,因此對手中沒有攝影機的台灣觀眾而言,當他們要相互討論曾經看過/聽過的影像時,就只能憑藉這些經辯士暗語重構而來的「非物質電影」(陳界仁語),依靠收藏在每一個人心中的「殘像」來交流。換言之,對陳界仁來說,台灣電影史的起源恐怕要從這些僅存在於記憶與想像之中的「非物質電影」寫起;而「沒有影像機具」這項外在條件的困境,反倒是台灣電影史脈絡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特質。
我想不只是電影史,整部台灣攝影史書寫也都必須審慎考慮那些未能顯影的、沒能即時建檔並保存的,甚至隨著記憶褪色消失的無機具影像。因此在一般常規的(可見、可感的)攝影史之外,其實尚有另外半部的潛在歷史,等待影像創作者與研究者的考掘與重估。由此觀之,「迴返計畫」裡念茲在茲的記憶迴返問題,不正是對台灣如此特殊之影像史起源的一種積極回應嗎?或許更適當的說法是:恰恰是因為創作者們殊異的美學經營與追求,從來不曾止步於現實影像的有限層次,如今我們才能深刻體認到影像、文字、聲響與記憶之間,有著極其複雜且不可分割的緊密關係;無論是陳敬寶、張照堂還是陳界仁,他們都試圖透過靜態或動態的影像創置提醒我們,唯有穿越視覺的表象,一部完整的影像史書寫才可能擁有顛撲不破的深厚根基。
註1 郭力昕,〈迴返人的主體性〉,收錄於陳敬寶攝影集《迴返計畫》(新北市:陳敬寶,2015),頁2-4。
註2 關於張照堂〈非影像筆記〉的攝影美學意義,請參閱拙文〈從直接攝影到「非影像」書寫:以張照堂影像美學和〈非影像筆記〉為線索〉,《現代美術學報》2014,27期(05),頁105-129。
註3 見陳界仁,〈影像與聲音「從翻轉到質變的行動」:從《蔣渭水:台灣大眾葬葬儀》紀錄片談起〉,《新美術》2013,2卷,頁4-23。
倫理的界線
在閱讀陳敬寶的「迴返計畫」及其攝影實踐時,有個至為關鍵的面向是值得我們思考的: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關係的微妙拿捏。甚至我們必須說,正因為攝影家採取的是編導式攝影,「迴返計畫」的內部其實存在一條具有危險性的倫理界線,若是無法謹慎而細膩地處理,那麼此一計畫的核心主題:「孩童」及「校園生活」恐怕便不是我們今日看到的豐富成果。

陳敬寶│湖東計畫:馬背遊戲 Inkjet print、文件
102cmx122.5cm、30cmx21cm 2011
102cmx122.5cm、30cmx21cm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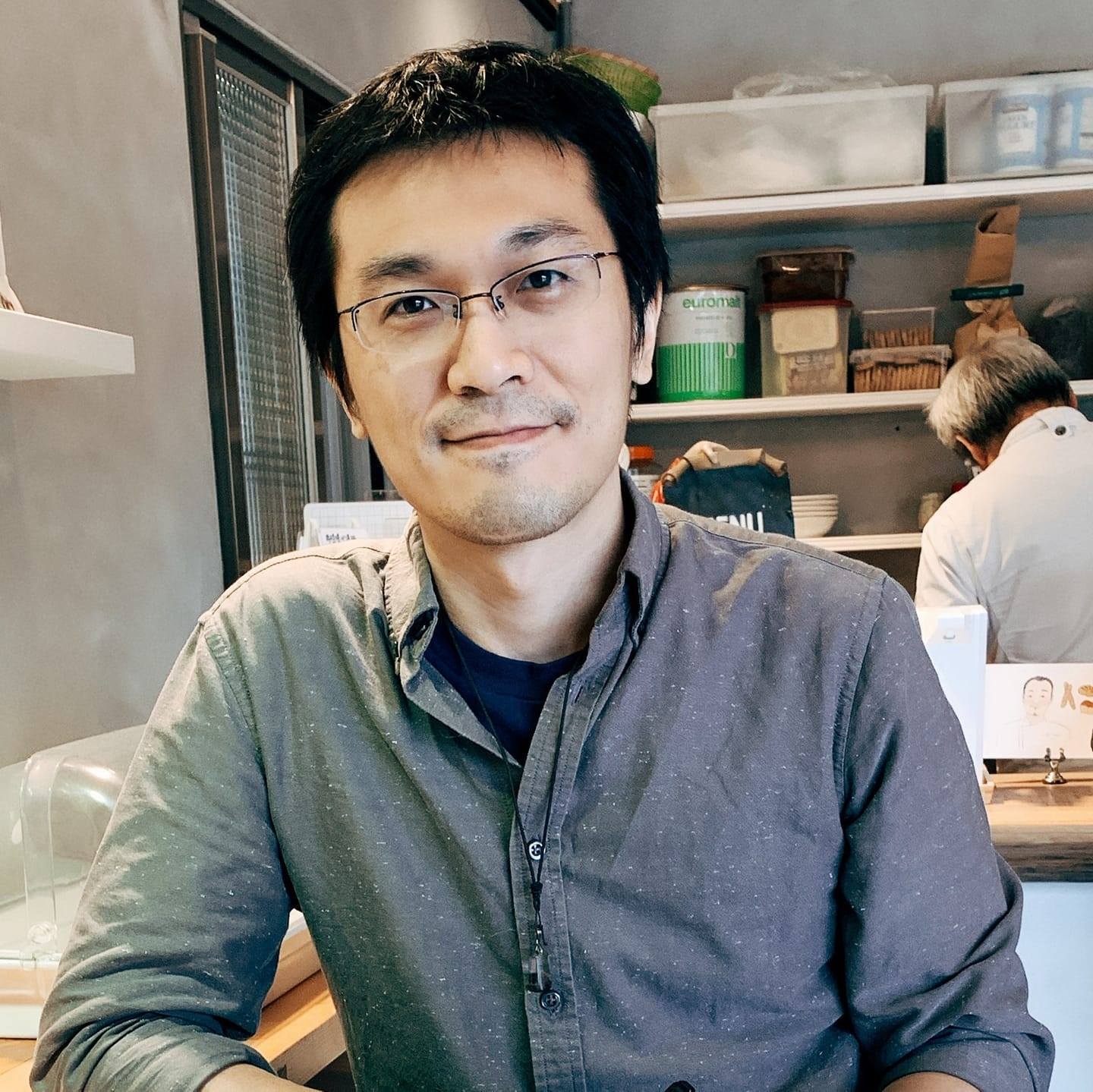 王聖閎( 13篇 )追蹤作者
王聖閎( 13篇 )追蹤作者藝評人,現為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任台新藝術獎提名觀察人(2017, 2018, 2021)。主要研究興趣包括當代錄像、行為表演及身體性創作;關注當代加速度政治下的生命政治課題,聚焦於科層機器對身體行動和耗費模式之影響,並且在此基礎之上,持續反思在地藝術理論的生產與擴延。文章散見於《典藏今藝術》、《藝術家》、《現代美術》,以及台新藝術獎「ARTalks」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