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愛戀式的供養體系
任何一種針對當代藝術生產模式與機制運作的嚴肅分析必定都會深感困惑:這樣的機制究竟是如何存活延續至今的?但所有深陷其中的人其實都清楚答案,因為這是一個全面仰賴非典勞動與志工制度,以及藝術工作者之自我剝削才有辦法支撐起來的例外經濟體。無論是國外還是台灣,藝術工作者的收入長期低於貧窮線早已不是新聞。為了展演發表的理想,經費預算與人力資源上的窘迫總是能以自主奉獻、情義相挺的友誼交換式勞動網絡,以及各種無限度且難以計算的犧牲耗費來補足,形成無法用一般行業生產特徵來審視、評估的另類經濟交換模式。
原本,藝術工作者的自主犧牲是為了跳出一切穩固僵化的框架,從社會結構、科層組織、法律制度、工作倫理,甚至是職涯規畫的既定軌道上偏移,以換取並保有流動性、能動性、彈性、自由等價值。
但活在非典勞動年代裡的藝術工作者卻會發現,馬克思(Karl Marx)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當年對資本主義所下的著名論斷:
「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6
早已變本加厲(註1),成為混亂世局中唯一明確的勞動圖景。
但這裡我們要談的並不是工作型態的瞬息萬變,或者缺乏耐心的熱錢於世界各地流竄等一般常被談論的新資本主義文化現象,而是當代藝術本身也學會以「彈性」和「變動」做為產業發展的基本策略。年輕藝術工作者若想要在這個環境待下來,就必須忍受未來前景模糊的不確定狀態,以及充斥短期時程(short-termism)思維的工作條件;唯一能令她/他倖存的只有各種因應展演活動而出現的臨時工、短期專案、勞務外包機會,得依靠生產結構邊陲的一點零星資源與補助來生活。再者,他們絕大多數都必須找尋另外一份與藝術或近或遠的副業,從其他領域所獲取的外部資源來「供養」機制內部的展演生產,形成一個機制本身並不追求經濟效益,而是由其成員想盡辦法支撐它的「供養體系」。這種供養體系的核心運作引擎不是別的,正是一種「藝術愛戀」式的延遲回饋,有點類似新教倫理的「延遲滿足」(deferred gratification)概念:做為藝術工作者的你必須自持克制,忍受所有生活與精神上的剝削磨難,因為你應當專注的是如何堅持自己的藝術理念,直到它在未來的最終兌現,無論那是無形的文化資本還是看得見的經濟報酬。但是勞動結構的大量非典化,使年輕後進的工作經驗愈來愈碎裂,同時也愈來愈難整全地重塑其生命敘事。於是,「彈性」成為禁錮枷鎖,「變動」成為永恆牢籠,愈是對藝術充滿熱情與愛戀的年輕工作者,反而愈無法逃離非典勞動的全面性反噬。

視覺藝術生態失衡的潛在危機
但嚴峻的問題還不只如此。若我們仔細檢視近幾年藝術相關系所對外公布的招生狀況,會發現潛在危機不只是勞動結構,還包括各種藝術專業分工與不同人力資源的日漸失衡。這些年來,人文學科所面臨的普遍性困境已被討論多時,從今(2015)年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董事會因為打算廢除人文學科,導致該校學生發動佔領大學的激烈抗爭運動(註2),到日本文部科學省(相當於教育部)要求國立大學應將人文學系廢除,或轉型成與企業及社會需求更加契合的課程方向(註3),都使得「文組無用論」的陳舊論爭再次浮上檯面。台灣雖無裁撤人文學科的類似新聞,但是大學氾濫所導致的高教崩壞問題、碩士學位貶值,以及就業市場緊縮等因素,確實使歷年來研究所整體報考人數逐年下滑。當然,其背後成因複雜,大學畢業生選擇報考實質待遇福利較佳之公職,碩士不再是生涯規畫必然選擇,以及各校碩士班甄試名額增加也都是原因。但這依舊無法改變晚近一、兩年,部分系所報名人數屢創新低,甚至必須甄試加上筆試才有辦法突破個位數的窘境。

其中,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最有機會培育出「非創作者的藝術專業人才」的系所狀況,尤其以藝術史、藝術理論研究的報名人數銳減最為嚴重,如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美術史組與理論組,104學年度的報名人數都只有97學年度的1/3甚至1/4少。相較之下,藝術行政管理與博物館學系所的人數衰減幅度則較為平緩,如台灣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文化政策管理研究所97學年度為90人,103學年度為47人,104學年度回升為89人;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博物館研究所101學年度報名人數分別為107人與60人,104學年度則降為86人與36人。有趣的是,不同於這些系所在招生上的日益困難,各個創作研究所的整體報名人數幾乎都維持平盤,甚至因為甄試而增加,顯見即使景氣不佳、各方面生存條件甚為嚴苛,但是嚮往成為藝術家的年輕創作者卻沒有減少太多。
上述的現象與數字,或許仍不足以斷言視覺藝術領域裡的非創作者人才正在一點一滴流失,但卻可能是種警訊。我們顯然應當追問,雖然青年貧窮化的問題遍布整個藝術產業,但在這個狹小的生態裡,每一種藝術工作者各自能獲取的資源與援助又是如何呢?我們曉得,創作者雖享有相對多的補助、駐村及獎選系統的關注機會,但創作本身就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一旦被狹窄的晉升天梯或主流品味所排擠,他們依舊必須依靠各種副業來維繫理想,甚至必須放棄創作,與其他非創作者一樣競爭各種行政、製作、執行的工作。至於藝術(文化)行政、經理、佈展、評論及策展等非創作者人才,雖然有公務單位的職缺可選擇,但並非所有人都志在公職;地方文史館、博物館的工作重心也未必是當代藝術。除了藝術媒體、畫廊產業、基金會、學術機關尚有僧多粥少的工作機會以外,這些年輕工作者同樣必須面對就業市場僅有大量非典勞動職缺可選擇的殘酷現實,卻不像創作者還有些許補助管道能做為後盾。總而言之,尚未被我們嚴肅看待的問題是:當前藝術生態的支援系統是否僅鼓勵某類藝術工作者留下而排拒其他人?同時,此一問題是否會隨著少子化的到來,以及就業市場的扁平化、均質化甚至劣化而愈趨明顯?

扁平化的彈性組織與中間層工作的消失
關於這點,需要進一步拓展文章開頭「當代藝術機制究竟是如何存活延續至今?」的核心提問。讓我試著把問題更加明確化一些:為何視覺藝術領域可以依靠少數的決策階層與正職人員,搭配上大量且高流動率的外包/臨時雇員、實習生及義工,就能支撐起所有展演活動的必備人力?除了眾人已熟知的「工作過量」、「情義相挺式的勞動交換網絡」這類答案之外,尚有一個線索值得探究,意即藝術產業所創造出來的工作種類與數量。我們可將當代藝術的勞動結構粗略劃分成三個階層:
(1)「上層工作」多半門檻高、職缺數量稀少,但是工作穩定且流動率低,如大學教授、美術館館長、藝術總監、機構負責人或高階主管皆屬之。
(2)「中間層工作」指的是如藝術雜誌編輯、藝文記者、基金會專員,或者各類政府或民間文化機構裡的正編人員。不過現有的中間層工作多為公家機關職缺,民間機構裡的工作數量不僅稀少,且往往一旦消失便很難再有(譬如日前藝術雜誌《藝外Artitude》的收刊,市場短期之內很難再創造出類似的職缺。)
(3)「基層工作」即是我們所熟知的各類兼職助理、臨時佈展人力、實習生等,它們往往是流動率極高的非典勞動工作,但卻是藝術就業市場釋放出來的主要職缺類型。
台灣現有勞動結構及生產網絡,多半因為預算規模小而呈現碎裂化的型態。再加上補助系統也傾向杯水車薪的人人有獎方式,使藝文組織朝向更為分眾、微型的發展道路。其次,由於展演活動確實存在許多不確定的變動因素,因此許多工作室、藝術團隊,甚至是中型藝術機構的組織型態,往往會傾向「任務/專案導向」的勞力編制,搭配必不可少的幾個正編職缺,最終形成一種扁平化的彈性組織來因應瞬息萬變的展演活動需求。這種組織型態的扁平化/去階層化(delayering),有點類似社會學家桑內特(Richard Sennett)在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科層組織(如跨國企業)所說的,機構為求能夠快速因應市場之變動,使內部結構趨於臨時化、扁平化與非線性的安排。(註4)當然,許多當代藝術機構並非跨國企業,但運用大量非典勞動之目的卻可能是類似的,因為這種彈性組織有其優點,包括人力配置簡單、權力集中、頂層決策傳達快速、應變能力佳、成本負債壓力低等。但其所帶來的惡果也顯而易見,特別是在藝術生態裡,由於有限預算多半僅足以維持極少數的正編人力,因此就業市場上的中間層工作數量日益減少、薪資水準長期停滯,往往還必須擔負兩至三人的過量工作。一旦組織運作的客觀條件更加惡化,取消中間層工作並改以大量臨時人力支應是常有的事。
必須特別指出的是,相較於非典勞動的道德問題,中間層工作消失所帶來的真正傷害其實是藝術生態整體的經驗斷層。因為這些職位多半要求數年以上的工作經驗,理應是一位處於25至40歲之生涯關鍵期的藝術工作者,在深耕專業、累積人脈網絡時最可能擔任的職務。但我們的環境卻經常一方面要求專業表現,另一方面卻讓這一輩的年輕工作者長期處在不穩定的,甚至是免洗筷式的勞動狀態。即使稍有豐碩資源,這個怪異的供養體系卻傾向人的(自我)犧牲以成就展演活動或作品本身,甚少將資源投入中間層工作的再創造,使更多年輕工作者有機會在穩固且連續的經驗中發揮其所長。換言之,當代藝術時常忽略人才是真正的資產,特別是那些能令展演活動運作順暢,其無形的工作歷練、默契與敏銳度都不易傳承的幕後工作人員。在持續開創工作機會這點上,顯然仍有不少進步空間。

尚待轉念的藝術生產模式
或許會有人反駁,民間藝術組織的預算稀少,因此本就只有資源相對充裕的公家機關有能力創造穩定的中間層工作。以臺灣目前窘迫的大環境而言,這確實是事實,但並非全部事實。晚近十年的台灣當代藝術,無論是生產模式還是創作型態都日益多元複雜,且隨著與國際藝術機構的頻繁交往、大型雙年展的策辦,愈來愈多展演活動需要仰賴多方專業團隊的協力合作才能促成,因此有不少相應而生的專業佈展/策展/設計/製作公司或小型工作室依存在藝術機制的周邊,顯示確實仍有少部分的新工作類型被創造出來。(如《典藏‧今藝術》畢業季專輯過去曾報導的專業布展公司「藝術戰爭公司」。)我認為,藝術生態是否具有活力的真正指標,就是民間藝術組織對中間層工作的持續開發。同樣地,其人才流失危機關鍵也恰恰在此。但遺憾的是,由於過度依賴扁平化的彈性組織,當代藝術早已養成美其名是精簡,實則是建立在錯誤預算思維上的僵化生產模式。公家機關一方面利用展出者自我剝削的勞力配合,另一方面又倚靠大量免費或薪資低廉的志工/工讀生來支應展演活動所需人力,形成一種「以為僅憑短少預算便可辦好一檔展覽」的錯誤認知與想像。民間藝術團體也不遑多讓,不少展演活動只知延續單一作者聖像化的舊思維,或四處複製藝博會的商業模式,卻從不思考這種欠缺思考與創造力的作法,只會更加排擠任何不符合畫廊空間展呈邏輯的藝術實踐類型。令人不得不質疑,當代藝術是否已狹隘到以為藝術經濟就等於畫廊經濟,機會就等於藝博會的地步?
總而言之,扁平化彈性組織所帶來的藝術勞動非典化,再加上我過去曾談論的「藝術明星」製造迷思,以及缺乏反思的展覽生產失控迴圈,是台灣當代藝術困限在短效思維裡而無法自拔,並且疏於探索其他經濟交換模式之可能性的三大主因。不破除這些窠臼與困境,當代藝術自然無「產業」可言,因為這個供養體系既無法吸引年輕後進持續投入,也愈來愈難讓那些熱情仍未油盡燈枯、尚有動力與意志做些突破的藝術工作者留步。這些都是藝術愛戀燃燒殆盡之後,我們依然無法迴避的殘酷事實。

註釋
註1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6
註2 見學生自組的「Humanities Rally」活動網站:humanitiesrally.com/about/(瀏覽時間:2015.09.12)
註3 中央社報導,〈廢除人文學系 日本26所國立大學擬實施〉,「中央通訊社」,2015.04.09。(◎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508250002-1.aspx),網頁擷取時間:2015.09.12。
註4 Richard Sennett, The Culture of the New Capitalism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47-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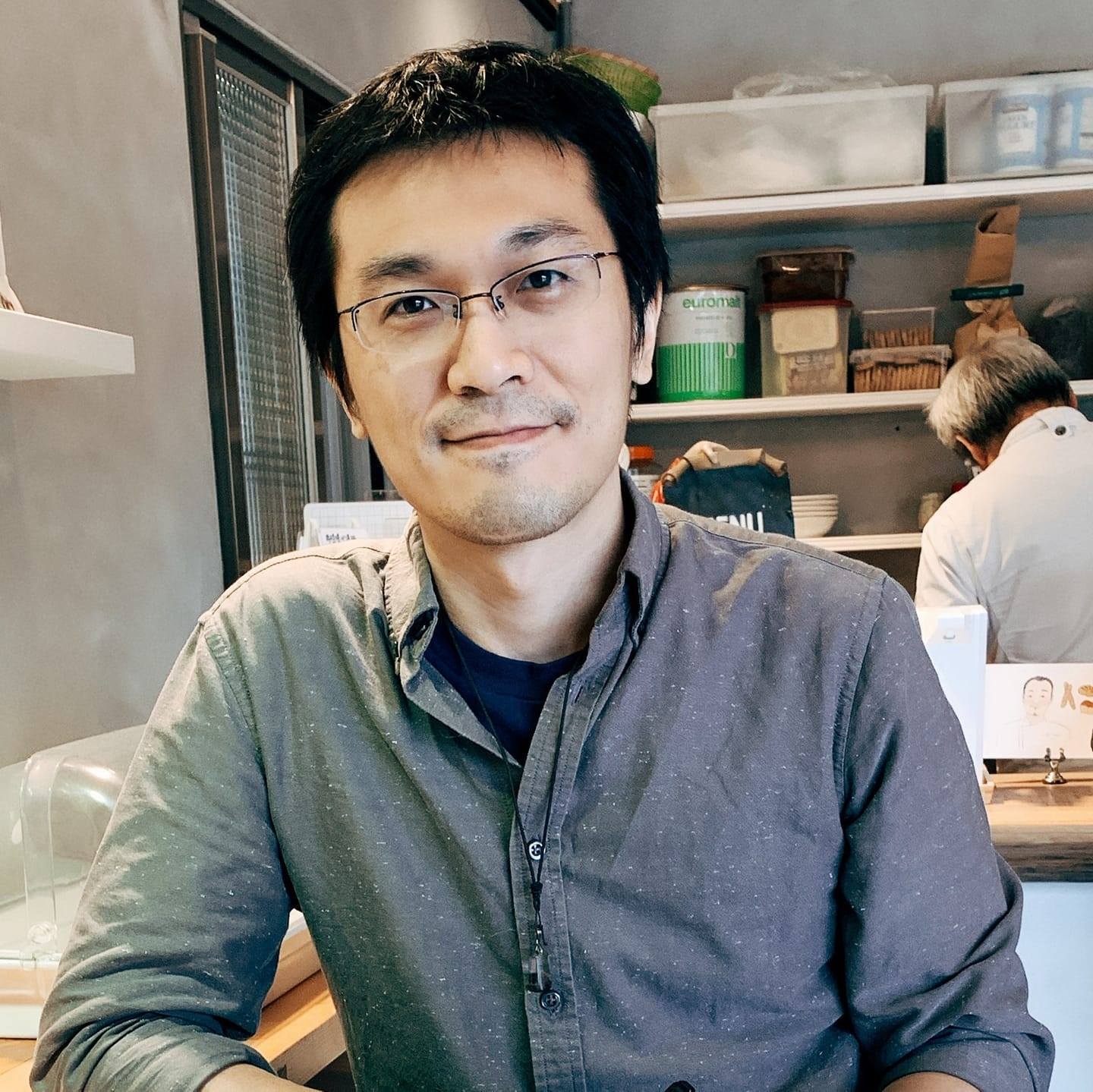 王聖閎( 13篇 )追蹤作者
王聖閎( 13篇 )追蹤作者藝評人,現為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任台新藝術獎提名觀察人(2017, 2018, 2021)。主要研究興趣包括當代錄像、行為表演及身體性創作;關注當代加速度政治下的生命政治課題,聚焦於科層機器對身體行動和耗費模式之影響,並且在此基礎之上,持續反思在地藝術理論的生產與擴延。文章散見於《典藏今藝術》、《藝術家》、《現代美術》,以及台新藝術獎「ARTalks」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