頓挫藝術、政治性及亞洲藝術參照網絡
如果說2006年之前,以世界圖景或全球化為潛在關鍵字的北雙,基本上仍置身在一個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理論尚未退燒的時空背景裡;那麼2006年之後,台灣當代展覽問題意識的焦點顯然已有所轉向。當時具指標性的事件我認為有二:一是徐文瑞和瑪蘭.李希特(Maren Richter)2006年底於台北當代藝術館策畫的「赤裸人」(Naked Life)。這檔展覽不僅具備雙年展等級的參展名單規模,策展論述對義大利哲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理論的援用引介,也將舊有的主體性問題移轉至諸如主權的懸空割讓、「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生命政治(biopolitics)等當代政治學理論的領域。在徐文瑞再次回鍋擔綱2008年北雙策展人所發表的〈2008台北雙年展的概念化及全球在地文化政治〉裡,他很明確地延續自「赤裸人」而來,聚焦於反全球化運動、「治理性」(gouvernementalité)議題,以及藝術政治性的論述取徑。同時,他也主張透過雙年展平台對他方藝術徵候發聲以彰顯自身說話位置的方式,來回應始終存在於北雙內部的主體性焦慮。(註5)
其二是策展人林宏璋2007年初策畫名為「頓挫藝術在台灣」座談會。在他同步發表的〈導論:瞧!這個癥狀〉裡,不僅接續「赤裸人」對當時台灣藝術圈政治冷感的問題意識,同時也企圖將時下年輕世代「自我表現卻又喃喃自語的寓言狀態」,與一種「特意規避政治力」、「所欲無可為之」、「困頓、沮喪於現狀」的徵狀相連結。(註6)儘管在當時,「頓挫藝術」的反式話語激起不同創作世代之間的論辯,以及對於年輕創作者詮釋模式的爭議。(註7)但它對日後台灣藝術圈積極強化藝術家的社會參與,確實起到推波助瀾之效。(2009年「景美人權文化園區事件」更是標誌著台灣藝術圈整體創作氛圍的深刻轉變,不僅向社會現實快速傾斜,也更注重藝術家對各種重大公眾議題或文化政策的積極參與。)
不過,若要深論台灣當代藝術裡政治性的缺席或重新在場,恐怕仍須就我們的現代性經驗及其背後複雜的歷史意涵,展開有別於西方現代性詮釋框架的梳理。誠如龔卓軍在〈惡性場所邏輯與世界邊緣精神狀態〉所言,「東亞現代性帶來的『世界邊緣精神狀態』(borderline),並不意味著據持西方觀點的靜態診斷,而是反過來看,這種東亞歷史焦慮與歷史意識還是要透過具有感覺重新分配威力的作品及評論來呈現。」(註8)某方面來說,2012年北雙「現代怪獸/想像的死而復生」適時提供這種「具有感覺重新分配威力」之作品及評論的聚集平台。且透過六個「微型博物館」樹狀式的策展權力結構下放,藉此引入諸如港千尋、洪子健等東亞或亞裔策展人的研究觀點,從而打開具有亞洲歷史/藝術史橫向比較視野的閱讀網絡。不過,假使我們同意2012年對現代性的重新聚焦,切中此時此刻台灣藝術圈對歷史問題意識及亞洲藝術參照網絡的高度興趣,那麼如今回看「1998台北雙年展:亞洲當代藝術研討會」的討論題綱,會發現儘管當時以區域性雙年展出發的策展定位,並未擴及東南亞現當代藝術的作品取樣,但是其所奠定的問題意識仍很貼近當前台灣藝術發展的務實需求。

2000台北雙年展「無法無天」展覽一樓通道,圖為庫索旺(Surasi Kusolwong)作品《通通20元,渾沌極簡》。(台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簡言之,北雙過去走上一條忽略其自身內在區域性格的道路。而在雙年展林立的今天,基於市場區隔之壓力,它可能也無法再回頭與國美館的亞洲雙年展、關渡美術館的關渡雙年展多年深耕的亞際藝術交流網絡相比拼。選擇繼續追逐「內在歐美性」(龔卓軍語,註9)並回歸單一策展人制的北雙,如今面臨的最大困難依舊是西方明星策展人挾其全球化的理論知識進場,卻無法在短時間之內細緻分梳亞洲諸多區域之作品選件彼此間的文化差異。又或者,相較其原本工作地域所累積出的外國作品清單,後加入的本地藝術家創作往往只能放在一種寰宇主義式的詮釋框架下,才具有初步的解釋力。如學者陳貺怡在〈雙年展策展中的理論生產〉一文中對2014年北雙「劇烈加速度」的批評,「人類世」(Anthropocene)概念的提出固然有布希歐(Nicolas Bourriaud)原本理論關懷的高度和創見,但由於與藝術家之間缺乏足夠的熟稔及共事時間,十位台灣參展藝術家的作品放在策展論述脈絡下,多少顯得有些不著邊際。(註10)其次,由於欠缺對在地社會脈動的充分掌握(2014年3月才剛爆發318學運),布希歐的論述最終只能停留在單向輸入的狀態,仰賴曾經參與相觀展演活動的論述工作者轉譯,卻難與台灣藝術圈近年亟欲回應迫切現實的問題意識產生有效的觀念對接,實為可惜。
走筆至此,2016年北雙「當下檔案.未來系譜:雙年展新語」也已開展。此時此刻,「我們究竟需要什麼樣的雙年展?」的問題或許早已跨越過往「國際/本土」、「全球/在地」的二分思考架構。但做為一檔必然會內化至我們歷史血脈裡的年度藝術盛事,台北雙年展的重要意義不只是每兩年一次外部觀點的引入,好藉此帶動跨區域交流,以及藝術社群討論的更新;在與台灣當代藝術核心關懷相互連結的論述工程中,它恐怕還必須扮演更主動、積極的角色,否則每屆互不相涉、節目單式的策展主題,只會留下諸多策展問題意識的斷裂。而這點遺憾,並不是單方面倚靠在地藝術史工作者、策展人以及藝評人的努力就可以補足的。
註1 蕭瓊瑞等著,《1996雙年展.台灣藝術主體性》,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1996,頁34-55、87-90。
註2 簡子傑,〈從主體性到衰敗身體:1996至2006年的台灣當代藝術關鍵字(二)〉。伊通公園網站。◎www.itpark.com.tw/people/essays_data/106/299。(瀏覽時間2016.09.14)
註3 黃寶萍,〈制度?經費?台北雙年展怎麼走下去?〉,《民生報》,2004.10.29。
註4 黃海鳴,〈雙軌制台北雙年展的思考─交流展現平台/凝聚社會想像及啟動話語行動的機器〉,《現代美術學報》,28期,2014.11,頁34。
註5 徐文瑞,〈2008台北雙年展的概念化及全球在地文化政治〉。2008年台北雙年展網站。◎www.taipeibiennial.org/2008/News/NewsContent.aspx?NewsID=iWtQXTY5yerSII9xW63dlBB5UrnuR26O&Language=iWtQXTY5yerWZqo3gg8/BL9NEiKjGqNL。(瀏覽時間:2016.09.15)
註6 林宏璋,〈導論:瞧!這個癥狀〉,《典藏‧今藝術》174期(2007.03),頁125。
註7 請參見拙文,〈一個更為滿盈與匱乏的生活世界:或從「新世代藝術家」的詮釋問題談起〉。伊通公園網站。◎www.itpark.com.tw/people/essays_data/633/738(瀏覽時間2016.09.15)。
註8 詳見龔卓軍,〈惡性場所邏輯與世界邊緣精神狀態〉,《典藏今藝術》,174期,2007.03,頁126-129。
註9 龔卓軍,〈我們內心那頭怪獸,歐美性:論台北雙年展的雙年展想像如何起死回生〉,《現代美術》,165期,2012.12,頁18-31。
註10 陳貺怡,〈雙年展策展中的理論生產〉,《現代美術》,175期,2014.12,頁6-15。
主體性,及其衰頹
如果回顧台北雙年展(以下簡稱為北雙)的歷史,我們會發現最有意思的論述源頭,正是一篇如今讀來仍鏗鏘有力的〈1996雙年展共同宣言〉。這篇由「1996年台北雙年展籌委會」共同屬名的短文,一方面開宗明義點出台灣做為「一個具有亞熱帶熱情、海洋文化開放包容特質,融合了中原文化、台灣民俗文化、原住民文化以及異國文化精神的文化主體」已有獨樹一幟的文化特質與社會風貌,因此對「台灣藝術主體性」的思考並非一種籲求,而已是對既存實況的必要梳理。但另一方面,這篇宣言及當年出版的兩冊展覽專刊內的諸多專文,皆可隱約讀到強烈的文化焦慮;世紀末,關於全球化浪潮的討論山雨欲來,參與當時論述建構的幾位作者們,字裡行間皆透露出一股亟欲為台灣主體性內涵定調的企圖心。彷彿唯有如此,台灣藝術主體性才能獲得穩固的基石,不至於繼續困囿在大中國意識與西化驅力的擺盪之間,也不至於被新世紀多元歧異的外來藝術論述所淹沒。專刊中,如李俊賢的〈建構台灣藝術的主體性〉、謝東山的〈給台灣美術一個機會—營造新世代美術〉(註1)皆是如此。儘管對照當時展出作品,這種後設而概括的論述生產未必能夠細緻貼近每一個參展藝術家的創作脈絡。
1996年雙年展「台灣藝術主體性」是唯一同時亦是最後一屆,以主體性思辨為策展核心題旨的雙年展。1998年緊接登場的「欲望場域」先是轉型成以東北亞藝術面貌取樣為主的亞洲區域性雙年展。而自第二屆的「無法無天」開始,北雙便展開對於全球化國際藝術趨勢的追逐,以做為「全球藝術浪潮之資訊窗口與渠道」的定位自居。此後,「主體性」一詞及其相關問題意識快速退去,或至少,成為隱而不顯的論述潛流。1990年代初由倪再沁所開啟的主體性論戰及其後延思辨,彷彿也嘎然而止。關注此問題的藝評人簡子傑,曾以「主體性的衰頹」描述這個狀況。(註2)他指出,關於「主體性」一詞的消退有許多種解釋,一般人很容易將台灣經濟與國力的下滑視為主體性議題衰退的社會背景,但此種觀點背後有將藝術表現與社會實況簡化連結,落入一種「素樸的反映論」的危險。換言之,我們必須越過表面上的觀感判斷,直指論述結構或機制上的改變才找得到真正的答案。在該文後半,簡子傑選擇以「身體」後來在藝評論述與國外藝術潮流譯介文章中的大量出現,來思考主體性議題轉化的軌跡與去向。
本文則選擇就雙年展機制本身的遞變來加以解釋。2000年之前,北雙的前身雖然具有強烈的本土性格,但就梳理在地藝術脈絡、嘗試提出美學主張的角度來看,前期的展覽策略其實已在本地藝術社群當中,內化為一種對雙年展功能的基本期許,並與官方戮力追逐的「國際化」想像驅力形成論述與意識型態上的相互角力。換言之,主體性一詞表面上雖然消失了,但它早已化為針對雙年展定位及策展方略層次的內在抗衡力量。在往後每一屆北雙的相關議論裡,我們都能看到這種論述角力不斷的復現,直至今日。

「朗誦/文件:台北雙年展 1996-2014」中的燈箱,圖為1996年展出作品縮圖。(攝影/林怡秀)
世界圖景與「前衛」的消逝
伴隨2016年北雙登場,目前於北美館三樓舉辦的「朗誦/文件:台北雙年展 1996-2014」裡(以下簡稱「朗誦/文件」),有個格外有意思的展場設置。由於必須在有限空間之中,一目了然地呈顯歷屆北雙的樣貌,館方特別將其中若干屆的展出作品縮圖拼組成一面大圖輸出,並且裝置在幾個大型燈箱上展示。依據歷屆雙年展各國藝術家的參展比例,這些大圖輸出裡自然絕大多數都是外國藝術家的作品,但眼尖的觀眾仍能從中零星辨識出幾位台灣藝術家的創作。我認為,「朗誦/文件」裡這些宛如百納被一般的作品縮圖,正是以往北雙對於國際化想像的最佳視覺化體現:在一個琳瑯滿目的世界藝術圖景裡,台灣藝術家的作品恰如其分地參與其中,共同呈顯在世界各地的觀眾面前。但事實上,這塊藝術百納布並不會真正等同於世界藝術的總和,更多時候,它仍只是歐美中心主義視野下建造的奇觀電視牆;台灣藝術家必須先符合這些作品所展開之美學平面背後的內在邏輯,才有可能現身在世界圖景裡。至此,前述討論的主體性問題,已轉化成雙策展人制之下國際與本地策展人的話語權平衡問題。而其中的衝突,在2004年「在乎現實嗎?」台灣策展人鄭慧華退席抗議事件到達顛峰。因為在這場世界圖景的話語權角力中,「在地策展人從同台演出變成了暖場歌手,甚至到最後連唱自己的歌的權利都喪失。」 (註3)
誠如黃海鳴在〈雙軌制台北雙年展的思考:交流展現平台/凝聚社會想像及啟動話語行動的機器〉的分析,雙策展人制的原初設計本就是期許一位外籍策展人,挾其多年深耕、連結的國際藝術家人脈網絡,以及長時累積鑽研的藝術議題,帶領北雙獲得更多國際媒體的關注。因此當時「在乎現實嗎?」的主要內容,勢必是范德林登(Barbara Vanderlinden)足以在其他雙年展策展人遴選場合上勝出的多年籌備資料。台灣策展人在此先天不均衡的論述生產位置中,幾乎沒有太多籌碼。(註4)不過嚴格地說,外籍策展人雖能帶進更大地理範圍的作品選件,但無論如何仍有其工作、生活領域上的侷限性。此時,原本台灣策展人所具備的東亞地緣關係網絡和實務經驗,能夠補足外籍策展人在短時間之內,無法立即掌握在地歷史空間脈絡,進行深入的策展田野工作的缺陷。但因為論述生產位置上的平等結構幾乎不曾發生,因此不僅兩個相異背景的策展工作者之間的良性對話不易發生,所謂的「國際」,最終往往仍只是「歐美區域」的替換詞。
因此,在步入雙策展人制年代後的前幾年,為了補足北雙在朝向國際趨勢之後所遺留下來的在地藝術梳理工作之空缺,台灣陸續出現幾檔刻意與雙年展同期發動、甚至與之較勁的中型策畫展。這類展覽不僅擔負起匯聚在地創作能量的功能,甚至提供年輕創作者截然不同的發表空間。如2002年的「Co2台灣前衛文件展」即是典型。不過,「前衛文件展」似乎也是「前衛」二字在台灣現當代展覽歷史裡的最後身影,在展覽議題日漸趨向回應全球化浪潮底下,經濟、科技、政治,乃至於飲食、文化等重大變遷的同時,台灣在地藝術社群所使用的美學辭令和理論框架也有所轉變。如同「主體性」一詞的消退,「前衛」也已被視覺形式上某種「國際規格」的追求,以及另外一組更新或更迫切的問題意識所替換,譬如,藝術的政治性。

2008年台北雙年展大廳展覽現場,圖為阿根廷的藝術團體 「國際錯誤分子」(Internacional Errorista)的作品《我們都是錯誤分子》。(台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Tag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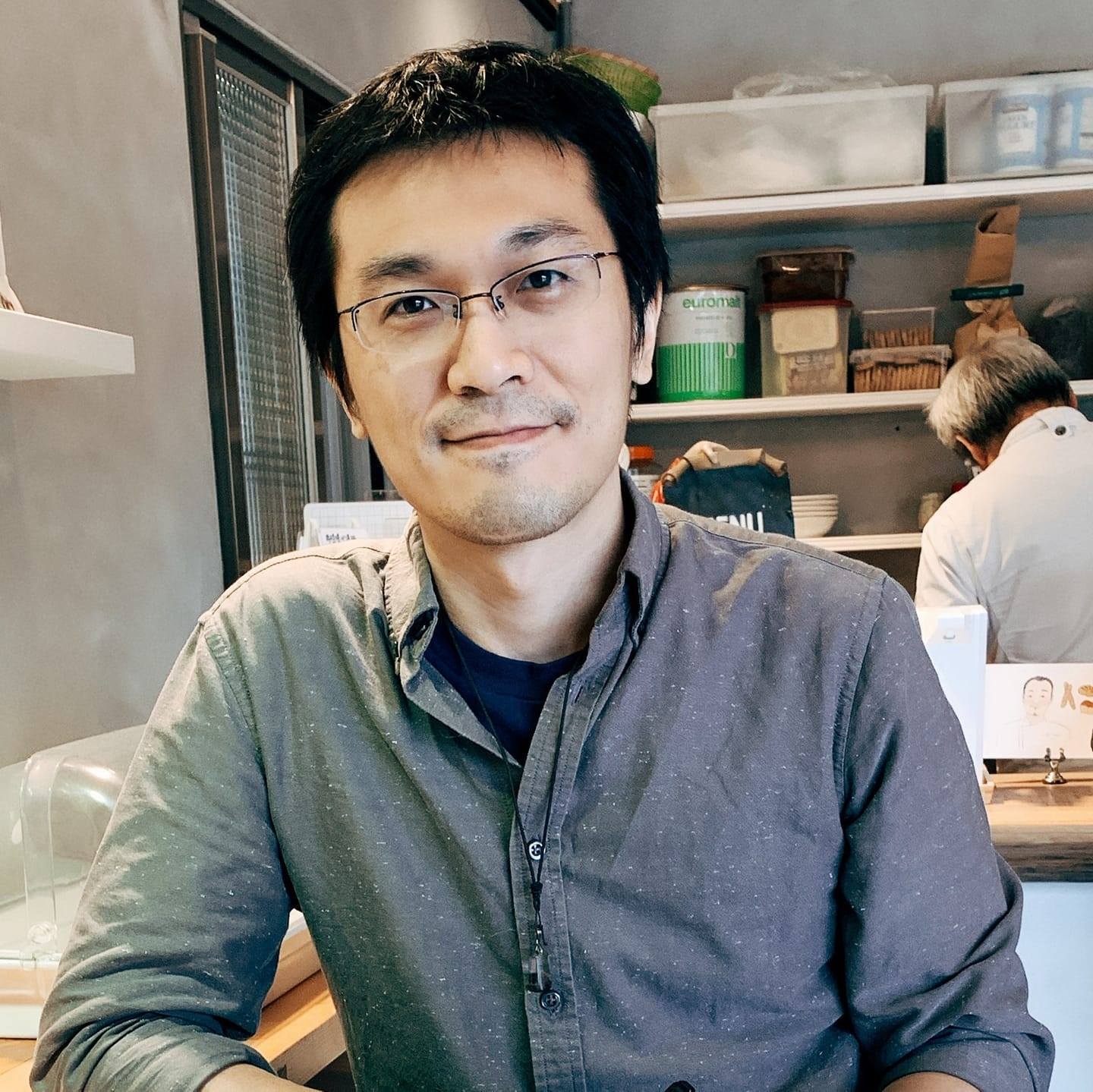 王聖閎( 13篇 )追蹤作者
王聖閎( 13篇 )追蹤作者藝評人,現為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任台新藝術獎提名觀察人(2017, 2018, 2021)。主要研究興趣包括當代錄像、行為表演及身體性創作;關注當代加速度政治下的生命政治課題,聚焦於科層機器對身體行動和耗費模式之影響,並且在此基礎之上,持續反思在地藝術理論的生產與擴延。文章散見於《典藏今藝術》、《藝術家》、《現代美術》,以及台新藝術獎「ARTalks」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