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命名,去現身。如果你不去命名,你就不具有文化歷史;一旦你不具有文化歷史,你便不存在。
—韓蒙(Harmony Hammond,註1)
初讀《踏青:蜿蜒的女同創作足跡》(以下簡稱《踏青》)的出版,讀者會立即與一系列既根本又棘手的思考難題對撞:為何在今天,仍有必要標舉「女同志」的標籤?如此的標籤還有其效力嗎?在創作上,它是一種類型劃分的概念嗎?以其為輻軸能為我們帶來何種殊異的創作/歷史風景?它是必須捍衛辨明的戰鬥集結地,抑或是創作者們亟欲逃離閃躲的枷鎖?特意返回一個明確而固定的認同標籤(而非人們更習慣聽到的多元、流變、混雜概念),會不會令《踏青》打一開始就走在一條充滿許多論述泥沼的古道上?

鄭文絜,Happy Birthday, Stranger!,2010「大女圖」參展作品,鄭文絜提供。
要回答這些難題,有必要稍微繞點路,從問題層次略有不同的女性藝術發展脈絡談起:台灣當前的女性藝術創作,早已跳脫古典的藝術史名冊顛覆策略,或者展覽性別參與比例的問題意識。早在1990年代中期,不少藝術家便已意識到女性藝術創作的可能弊病,譬如創作媒材與陰性特質之間過於簡化的連結,或者過於聚焦在性別議題上,以致於忽略與其他社會議題相互連結之能動性等問題。更重要的是,誠如許淑真在〈台灣當代女性藝術轉型之必要與困境〉(註2)中所言,女性藝術的「中產階級化」,使其往往著重個人解放/奮鬥史,創作上持續停留在自我觀視層次,卻看不見社會集體的生存困境、焦慮及衝突。一言以蔽之,女性藝術有淪為中產階級意識型態之利益維護工具,忽略階級與社群之問題向度的潛在危險,進而將自己困囿在一個封閉且難有對話空間的論域裡。因此,當代的女性藝術創作無不極力跳脫媒材形式與生物性別認同之標籤,也極力避免在分配政治的競逐過程中,重新鞏固了父權結構慣常標舉的那種英雄主義式的知識建構模式。其具體出路,即是轉向一種更著重社群培力、長期陪伴/伙伴關係,以及脫逸於既有展呈機制之外的實踐路徑;從社群參與實踐,擴及至文化地景與環境生態的議題鏈結。如侯淑姿近年的創作發表、吳瑪悧及竹圍工作室的「樹梅坑溪環境藝術行動」,都是這種社群轉向的典型範例。
然而,《踏青》一書所論及的女同志創作樣貌卻更形複雜,也更難描繪。因為女同志們蜿蜒曲折的足跡雖與上述脈動息息相關,卻不可簡單歸屬在女性藝術發展脈絡(的陰影)底下;其研究困境,是在尚未被細緻辨別、梳理、建檔之前,就已遭逢整個研究潮流不斷地往多重流變、自我解構之方向奔馳的緊迫局勢─甚至,直到《踏青》成書之際,都仍有藝術家深陷受訪即是現身的巨大焦慮。倘若如此,我們真能輕易地說,回望「女同志」之標籤已是不合時宜的逆流之舉嗎?誠如韓蒙所言:「20世紀已經有非常多的女性藝術家被注意,但是即使她們之中有些人是女同志,她們的性傾向卻不會被相提並論。這意味著這些女同志藝術家的同志身分如何在創作生命中扮演關鍵角色,是不被注意的…。」(註3)毫無疑問,情慾是真實的,認同焦慮是真實的,創作者在社會關係裡的緊繃或磨擦更是真實無比的。這些創作者的內在衝動與經驗細節,怎是一句類型化標籤便可輕鬆帶過的?由此觀之,《踏青》打從一開始就面臨著雙重挑戰:它一方面必須積極回應台灣女同志藝術研究百廢待舉的嚴峻現實,另一方面,卻也不能忽視女性藝術發展的當代轉型問題。而《踏青》對於創作者生命敘事分享的特意側重,可說是直面此雙重挑戰而來的編輯巧思。

吳梓寧,無視哀傷01-撕裂我,2010「大女圖」參展作品,吳梓寧提供。
整個1990年代,是台灣性別研究與同志議題蓬勃發展的黃金年代,無論是理論的引介還是論述的在地深耕,都有相當多元豐富的開展。不過這段時間的書寫成果尚有一大塊缺憾,意即,雖然我們有數量可觀的論述建構、個別電影/文學/劇場的作品探討,但由創作者口述之生命經驗回顧出發,繼而擴及作品背後的感覺結構、精神結構之分析的基本工作,卻仍舊鳳毛麟角。《踏青》的出版,可說正好呼應此一回望在地歷史的新問題意識。它從台灣劇場界裡女同志創作者的啟蒙養分做為考察起點,一路向外擴及至文學、電影、視覺藝術、音樂等範疇之中,不同世代的女同志創作者對歷史及作品的深刻反思,補足了1990年代以來,台灣現當代藝術史/劇場史/文學史等歷史考察工程的懸缺之處,讓我們的思考得以重啟。
由此觀之,《踏青》並非邀請我們毫不反思地回返(性別)類型劃分的政治泥沼,而是提醒我們:這些相互交織的脈絡細節,不僅是對女同志創作足跡的可貴補述,更是日後催生在地性別理論的必要沃土。其次,著重創作者口述訪談的方式也提醒我們,過去強調作品本身之獨立性的批評策略,固然可免去「出櫃」的複雜難題,卻也存在著去脈絡化的根本危險。因為刻意迴避創作者的經驗與意圖,反倒阻隔、甚至否定了恰恰是根源於性別意識而來的原初情慾與衝動。
最後,《踏青》提醒我們的是一種存有論層次的書寫意義:去指明一種身分、去捍衛一個戰鬥位置甚或生活方式,源自一種基本的抵抗,也就是對那種時時否定歷史閱讀可以擁有更多剖面和視角之傲慢偏見的積極抵抗。因為,如果沒有透過基本的口述紀錄、生命故事的描摹和摘取,以及歷史檔案的重新梳理,曾經存在的創作軌跡也只會湮沒在歷史廢墟的碎片裡。
據此,寫作的目的即是為了抵抗遺忘,因為書寫的戰場即是存有的戰場,書寫行動永遠都是美學與政治上沒有終點的抵抗行動。在此意義上,《踏青》向我們細細展示的,遠非女同志藝術研究諸多難題的終極解答,而是未來一系列歷史迴返之旅的必然起點。這些引領後人前行的鮮明路標或足跡,無疑是書中積極發聲之創作者及書寫者留予我們的最好禮物。

《踏青:蜿蜒的女同創作足跡》書封。(女書文化提供)
註1 語出韓蒙2011年於其工作室的一次訪談內容。詳見當代酷兒文化網站「We Who Feel Differently」,網址:◎wewhofeeldifferently.info/interview.php?interview=109(參照時間2015.12.28)
註2 許淑真,〈台灣當代女性藝術轉型之必要與困境(上)(下)〉《藝術認證》第19期,2008.04,頁92-95;第20期,2008.06,頁106-109。
註3 轉引自:凃倚佩,〈以「看見」做為一個起點:女同志藝術家吳梓寧、鄒逸真、鄭文絜〉,《踏青:蜿蜒的女同志創作足跡》,台北:女書文化,2015,頁152。
Tag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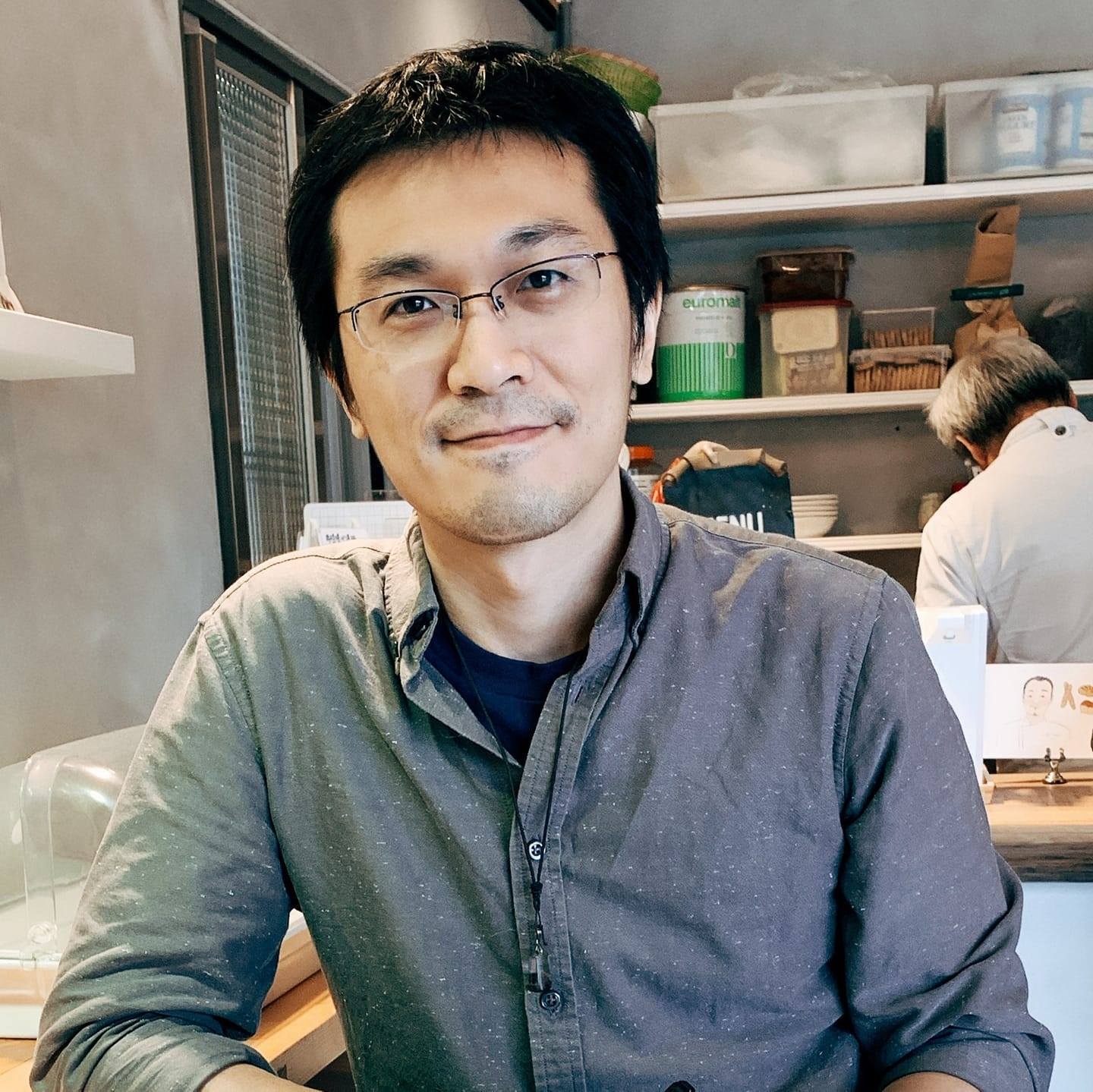 王聖閎( 13篇 )追蹤作者
王聖閎( 13篇 )追蹤作者藝評人,現為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任台新藝術獎提名觀察人(2017, 2018, 2021)。主要研究興趣包括當代錄像、行為表演及身體性創作;關注當代加速度政治下的生命政治課題,聚焦於科層機器對身體行動和耗費模式之影響,並且在此基礎之上,持續反思在地藝術理論的生產與擴延。文章散見於《典藏今藝術》、《藝術家》、《現代美術》,以及台新藝術獎「ARTalks」網站。

